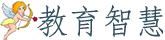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大雾又漫上来了,到处湿漉漉的,门窗非捂得严严实实的不可,否则墙上就得蒙上一层珍珠帘子,地上如同洒了水一般,怎么也擦不干,脚一踩,到处脏兮兮、滑溜溜的。可是,关死了屋子,空气凝滞成了一潭死水,叫人浸在里头,简直憋得透不过气来。
到了傍晚,天地还是连成一片,白茫茫的,像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状态。方然在工厂收了工,顾不得雾大难行,骑着电动车一个劲儿地往家跑。
她老公中午出门去了,家里的老公公正躺在床上害病,食道癌晚期,拖了大半年了,眼看没几个日子好活了。这漫长的三四个小时,他一个人呆在那座阴暗潮湿的老屋里,裹着那床散发着一股霉臭味儿的脏被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有多苦多闷哪。何况,这么一段工夫,他不知又得往床前的大盆子里吐多少血了。没人在一旁服侍,行吗?永远也清洗不干净,遇上这种天,想洗也洗不得。
幸好,这老头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们有空就回来帮帮忙,俩儿子俩儿媳排开了日期轮着日夜陪护病人。今儿轮到方然家,她怕回晚了出事儿,也怕妯娌生是非,急冲冲地推门进屋,看老头子去了。
老头子这两天已经不太能进食了,连喝两口米汤都费劲。他艰难地偏过脸来,眼珠子动了动,说不出一句话来。
方然觉出他面有难色,不用说,八成是大小便失禁了。从前给他换裤子都是男人们的事,他严令只让两个儿子负这个责。这下可怎么办?给他换吗?他不乐意;不给他换吗?他难受是一回事,万一一会儿小叔子小婶子过来,瞧他湿了裤子却没料理,不是要责怪她么?
方然一时慌乱起来,左右为难。迟疑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伸手进他被窝里一摸——天哪,果不其然,尿湿了!而且是连裤子带床地湿透了!我的妈呀,这是尿了多少回呀,怕有十几泡尿吧!
方然心里嘀咕着,心头早涌上了一种作呕的感觉来,便悄悄地咬了咬嘴唇,从橱柜里找出了一件干净的睡裤来。
她鼓了鼓勇气,让自己坚定起来,俯身对公公说:“俺爸,我给你换条新裤子吧!”
老头子使劲地哼了哼,听不清他要说点什么,但意思是明白的:不换。
“不换你多难受呀!这样泡着不行啊!”方然努力软了语调劝道,“再说窗外雾大得很,又开不得窗换不得气,你还这样浸着……”
这屋子浸在雾里,而他则浸在尿里。说实在,病人久在病室里,鼻子早失灵了,大概是没什么感觉的;正常人一进这屋里来,就免不了恶心要吐。
有什么办法呢?为人子女,为父母养老送终,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公公要她擦澡、换内衣裤,她有什么理由推脱么?即使外人能够谅解她,她自己良心上也是过不去的。换成自己到了这种等死的地步,不也得指着子女们来伺候吗?
方然狠一狠心,坚决求道:“俺爸,今天真不凑巧,舜仔(方然老公的名字)有急事出去了,不然也用不上我。我实在不忍心看你穿着湿裤子等他回来。你多熬一分钟,我就多受一分罪——我良心不安,对不住你老人家!”
老头子那张黯淡无光的脸,消瘦得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皮包着一颗头骨,什么表情也显不出来,眼睛里却射出抵触的光来,真是又可怜又可笑。
已经到了这种生死关头了,还在乎什么呀!又不是个帅哥美女,只怕春光乍泄。就是方然自己,生了两个女儿,两次都生得吃力得要命,还不是由着助产士把她当母猪一样摆弄的?甚至头一胎实在困难,还用的男助产士呢。
有什么办法呢?在你无法自理之时,在你生死攸关之际,“尊严”这种东西就自动贬值了。它甚至可以被踩到地上去,只要能叫人多喘一口气儿。邻居赵老太也是食道癌,人家肯治疗,管它插了一身管子,切断了所有肋骨,接上了一截塑料管,整个胃抬了上去……这么多年了,还活着呢。
她公公却打死也不肯上医院做这种手术。他坚决不让医生把他当畜生一样施救。就是眼下这湿裤子,还不肯让儿媳妇换呢。这头脑怎么想的!
方然真理解不了他。她暗地里听说过,她公公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多么守规矩的人,正经务农不肯,倒是喜欢坑蒙拐骗,还坐过好几年牢。后来又跟自己的亲弟弟闹了矛盾,欠债不还,跟人家绝交了三四十年,还是前两年她婆婆病危,临闭眼,才交代俩儿子拿出钱来还了债,跟人家化解了冤仇。这样一个人,一个没写过什么辉煌历史的男人,还真的讲究那点下半身的尊严么?
方然犹豫了半天,想不大通,就怕自己落得个“不孝”的罪名——叫外人指指点点是一码事,恐怕连老公回来都得朝她发脾气,她不得不下这个手。
“俺爸,你不换也得换。”方然硬了口吻说,“你自己受得住,我可担当不起!”
她说着,一把掀开了被子。只见她公公瘦成了一把骨头,大约有个五六十斤的样子,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好像小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松松垮垮、晃晃当当的,处处显出骷髅的形状来。
方然的心不禁怦怦地狂跳起来,既恐惧又怜悯,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垂死之人的复杂感情。她连忙把老头子挪出了湿掉的那一角,小心翼翼地要帮他脱下裤子。
不料,有个阻力使她扯不下裤子来——
抬眼一看,原来,她公公用两只鸡爪一样的手死死地拽住了裤腰!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拼出了最后的那点生命,两只手都在颤抖,整张脸都在抽搐,那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点上了两只小小的火炬,刚才还将熄未熄的眼神变得坚强不屈,仿佛他这一生所要抗争的就是剥夺他裤子的恶势力……
他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他的裤子,捍卫他的尊严!
方然大大地吃了一惊,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她不得不承认,人与人是不同的。是啊,人与人从骨子里就是不同的。
她赶紧收了手,拿被子把公公盖好,又在被子上轻轻地拍了拍,如同安慰一个三岁的小孩。
她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陪着公公等他儿子回来。
她想,等多久么,她都等得起。
她想,这一间大雾笼罩下的潮湿污臭的屋子,其实并不可恶。
【后记】
又过了不到两周,老头子咽气了。咽气前一天晚上,他自己打电话把110、120都叫来,控诉大儿子不孝——舜仔前些天把独占老宅的遗嘱弄到手了(他弟弟前几年买彩票中了60万,自个儿买了块地盖了个五层楼,在父亲和哥哥的磨蹭下,他同意只拿5万补偿,把两层半老宅赠给哥哥),两个妹妹虽气愤难平,也回来给他签了字,他就懒得再照料老父了,轮到他看护时,他净溜号!闹了一宿,第二天,老头子没了。一切都好了,终于可以给老人送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