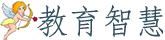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全美35位精神科医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根本无法领导美国。在公开信中,医生们描述特朗“情绪极度不稳”,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DP)。
一时间也引发了争议,有同行认为上述精神病专家可能涉嫌违规,此行为不仅违反了“戈德华特守则”(美国的精神病医生在亲自为病人诊断之前不能做出任何结论),也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我有病,你有药吗?
“你们觉得我有精神病吗?”
每次给心理系的学生上《异常心理学》课,我都问他们这个问题。
我希望他们理解,“诊断”的本质是什么。
学生们总被这个问题惊到,他们低头窃笑。也许有人真的觉得我有病。这是他们的权利。没关系,我不用理会。鱼说你怎么不在水下生活,你不合群;鸟也可以鄙视我不会飞,弱到爆。但这是他们的想法,跟我没关系。
但,如果一个精神科专家说我有病,我没办法不理。
退回几十年,这个判断有可能让我被关进病房里。假如我挣扎反抗,还会被套上约束带,打安定针,就算是亲朋好友也爱莫能助。即使现在,《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了诊断权的范围,我还是有可能因此面临一大堆的限制和麻烦。会有人听到医生的一句话,就认定我是异类,歧视我,排挤我。哪怕他们什么都没听说(我会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个诊断的秘密),我自己也会在心里恐慌:我还是不是正常人?要不要接受治疗?会不会有一天病情恶化,遭遇不测?
你看,我没办法对专家的说法置之不理。
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说的话,对我,以及更多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手握权力。注意,“权力”,不是“权利”。每个人都有说我有病没病的“权利”,但只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的说法才可以影响我的生活。
这种权力,叫做“诊断权”。
诊断,不只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带着权力的判断。
权力,是诊断的本质。
怎么理解这句话?
很多人以为医生做诊断的时候,只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是”或“否”,“真”或“假”,就跟做数学题一样。但事实上,数学题只是观察和推理。而医生在对某个人下判断的同时,不只是观察和推理,他同时要决定社会(或者说,法律和法规覆盖的,由暴力作为后盾的整个体系)该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个人: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需要治疗(甚至是强制治疗),不需要治疗,需要被隔离,需要被视为危险,需要接受处罚,或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而且,诊断的权力不只是如此。
诊断并不是去单纯“描述”一些客观存在的指标,就像这个人的身高、体重、白细胞的数量,它是在借助这些客观指标做一个分类。这个分类,无论参考了多少标准,引用了多少理论,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判断。
如果说生理疾病的诊断,还会参考大量客观的生理指标,相对显得更“与人的因素无关”一些的话,那么精神疾病的诊断,跟医生的主观因素,包括印象、观察、感受、经验、社会文化背景……关系是尤其密不可分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诊断的制订者(某些时候,甚至包括执行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主观思考,放到这个区分的过程中,影响最终的分类结果。
同性恋的例子就不用多说了。曾经被看成一种精神障碍,现在被看成正常人。他们本身的客观指标并没有变,只是制订诊断标准的人想法变了。
即使有了严格的诊断体系,同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不同的医生也有可能给出不同的诊断。有的说有病,有的说没病。怎么办?申请会诊。会诊得到一个更高级别的结论。有一点像是法院判案,有争议,就可以请更高一级法院给出结论。但这个结论也不是“客观”的存在,不过是更审慎的“主观”而已。
所以,诊断最根本的权力,是一些人有权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换一个好听的说法,则是“专业知识”),使得另一些人得到区别对待(treatment)。
这里还有必要多说几句。
有的人说:“但一个人有病,就是有病啊,怎么能说是主观的。”
他们以为,首先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诊断”标准,有些人就是有病啊。大家只是委托医生,用这个标准把这些人挑出来,对他们实行“治疗”。
但是,这个顺序弄反了。
“病”,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它的本质,是一个人为的分类体系。
古代没有诊断标准,人们照样对彼此进行分类。科学的诊断只不过区区几百年的历史,而人们区分出所谓正常和异常,普通和异端,多数和少数,恐怕已经有几千年了。记住,只在最近,才有了“诊断”这种东西。而长久以来人类一直都在把某些人挑出来,实行“治疗”(或其它各种各样的“对待”)。
好,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诊断,是人类最近发明创造的一个体系。
目的是为了把一些人挑出来,加以区别对待。
为什么要把一些人挑出来?
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通过区分,为病人找到适当的治疗,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质量。另外,也有可能减少他们家人的麻烦。也有时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比如给予“病人”多一点的关照和特权。还有一种原因,尽管有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它的确存在:就是“病人”本人未必能从分类中获得什么好处,但大多数“正常人”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不管是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还是强制“疯子”住进精神病院。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病是一种分类,而诊断,是实现这种分类的特权。
医生行使这种权力,来决定一些人受到整个社会的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样做对人(至少是大多数人)有好处。
好,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35位美国精神病学专家发表一封公开信,宣称特朗普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情绪极度不稳”,不适于担任总统职务。
这不是让我最震惊的。
最震惊的是,即使在同行指出这种做法不妥,违反戈德华特守则之后,这些专家仍然认为自己必须发声:“沉默将使得我们无法向媒体记者以及国会议员们提供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担心,继续沉默将付出太大的代价。”
完全是一副替天行道的样子。
谁是天?“我”(精神病专家)的判断就是天。
希望这是假新闻,或者是假的35个精神病专家。
否则的话,这些人就太疯狂了。
他们完完全全扭曲了诊断的意义,他们把这件事歪曲为:“某人有病,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了(但不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事实,按照伦理,我们还应该为这个事实保密。然而为社稷苍生计,我们不得不把它说出来。”
这真是一个充满恶意的歪曲。
我们说了,病不是天然存在的事实,病是一个有主观参与的判断。
它的本质,是挑选哪些人需要被区别对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需要对有些人(有时是我们自己)做出这种分别,便把这个权力授予了精神病专家。请他们运用专业技能(包含了他们的主观经验)替我们完成这个区分,并(通过卫生部、法规、社会舆论等方式)对他们做出的判断给予配合。
这个权力有多大呢?想一想“免除刑责”四个字。
如果一个人有权力判断你是不是一个“病人”……
这个人想帮你的时候,他说:“你有A病”。你就可以走绿色通道,所有人都会照顾你,给你额外的特权,让你可以免于为自己做的事负责。
这个人想毁你的时候,他说:“你有B病”。人人都会躲着你走,你取得的一切成就化为乌有,你说的话没有任何人相信(或当真),你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像是一个笑话,你本该有的权利被夺走,甚至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他有权让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同情你,照顾你,限制你,害怕你,轻视你。
极端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发明一些新的“病”,宣称你就是这种新病的患者之一。在中国临沂,这足以让一个人接受电击。或者,在最轻微的情况下,没有特别严重的后果,也会让你惴惴不安,担心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当然了,你说专家怎么会做这种事?专家都是有道德操守的。我完全赞同。然而这么大的权力,怎么可能只依靠道德来自律?项少龙老师名言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好能从规则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笼子一直都有,就是“医生的诊室”。
由取得专业资格的医生,在指定的行医场所,以符合规则的方式进行操作,才可以对人进行病理意义上的“分类”和“处理”。这是一直以来行使诊断权的约定条件。因为诊断事关重大,所以需要格外的谨慎。如果不是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样的区分(或者,在很少数的时候,允许由另一些人以慎重的方式,替代他做出决定),就不可以随随便便地对他进行这种分类。
正因为如此,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在1973年制定了戈德华特守则:“精神病医生只有在亲自为一名患者进行诊断之后,才能给出诊断结论。”
那35位美国精神病学专家,越界了。
特朗普这个人,我们可以不喜欢他,可以尽情嘲笑。觉得他丑,觉得他坏,觉得他愚蠢,觉得美国在他的领导下一定会完蛋,这些都没问题。
你觉得这个人有“病”?也没问题。
因为你是“觉得”他有病而已。这是你个人的一种感觉,就像你也可以觉得我有病。你并没有把它上升为一种权力,用来影响一个人可能遭受的待遇。不用拿它当回事。大不了你把它说出来,对方不服气,也说你有病就是。
已经有不少媒体和自媒体发声,说特朗普有病了。不少人都认为他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还有人对照了诊断标准(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买一本诊断书,看谁不顺眼,就找一个精神疾病一条一条拿出来对照),像模像样的。这话完全可以说,因为大家不是专家。他们的判断,就只是一个判断而已。
但是,精神病专家说这个人有病,就根本是另一个性质的事情。
因为他们真的拥有这个权力。
就像两个人吵架,互相说“信不信我打死你”,这只是吵架。但如果一个人真枪实弹地端着一把枪,再说“我打死你”,这就不再是吵架的事。
这些专家做的事,等于是说:“我们想行使这样一种权力,根据这个人呈现出来的某些特征,我们有权力号召公众对这样的人进行特殊限制。”
他们还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是在为正义说话。
这太可怕了。
当然,这事儿特朗普可能根本不在乎。
毕竟他不可能因为专家说两句话,就做不成总统了。
但就算如此,他多少也会遭到一点“病人”的待遇。以后人们会说:“你知道吗?特朗普是真的有病。”“谁说的?”“精神病专家,三十多个呢。”
这种待遇,如果落到普通人头上,意味着什么?
“你们觉得我有精神病吗?”
我在《异常心理学》课堂上提问。
“我是合法的精神科医生,”一个人可以回答我,“我觉得你有病。”
只要加上后面这句,我就惨了。不是“他觉得我有病”,而变成了“我真的有病”,或者说,他说出这句话,社会从此便可以对我作病人的对待。
这样的结果,可能发生在你我每个人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次,当你听到精神病专家或精神科医生走到诊室之外,试图对一个并不是他病人的人发表诊断意见,无论他讲得有没有道理,无论我们心里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见,只要他拿出裁断者的架势,就不行。他刚一开口:“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觉得这个人有……”,我们就要立刻制止他:
“闭嘴,回医院,做你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