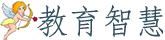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这首令人浮想联翩的诗歌,是汉朝乐师李延年献给汉武帝的,令汉武帝不仅感叹:
“世上果真有这样的美女吗?”
果真有。就是李延年的妹妹。
借助这首曲子,这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成为汉武帝最宠幸的妃子,李夫人。
她之所以获得汉武帝的专宠,不光因其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智慧。
进宫数年后,李夫人重病。
汉武帝来探访,她蒙在被子里不肯出来,并叮嘱汉武帝在她死后照料她的兄弟。
汉武帝允诺说,只要你见我一面,我会赏赐千金,并拜你兄弟为官。
李夫人却说,赏赐与拜官都取决于帝王你,而不取决于见我一面。所以,还是不见。
汉武帝怒,想掀开被子,李夫人哭泣,汉武帝只好作罢,悻悻离去。
汉武帝走后,李夫人的兄弟们感到惊恐,问她为什么惹皇帝生气。
李夫人解释说,我是因美貌而得到宠幸:“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而恩绝。”
假若皇帝看到我生病而不再如以前美貌的样子,对我的爱必然会减少,甚至会讨厌我,而一旦“恩绝”,你们还会得到皇帝的恩宠吗?
不久,李夫人病逝,而汉武帝果然对李夫人朝思暮想,甚至几次找道士为李夫人招魂。
一次恍惚间,以为真见到了她,因而发出了佳人为何“姗姗来迟”的感叹。
除了李夫人外,汉武帝最有名的另一个妃子是钩弋夫人。
那是汉武帝61岁时的一次出巡。
途中,他遇到一个少女。少女的双拳紧握,说是,出生后一直如此。
汉武帝令众宫女去掰,都掰不开。但汉武帝轻轻一掰就掰开了她的双手,并发现手心中有一个小玉钩。
她因而被称为“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得到了汉武帝的专宠,并生下了儿子弗陵。
汉武帝70岁,决议立弗陵为太子。但几天后,汉武帝便下令杀死钩弋夫人。
这时,钩弋夫人才24岁。
杀死她后,汉武帝问身边人:“世人怎么看待此事?”
有人回答:世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立其子为太子,另一方面又杀其母。
汉武帝感叹,蠢人哪里知道他的考虑。历史很多祸乱都源自“主少、母壮”,并且,年轻的太后还会骄奢淫乱,就像吕后一样。
女人是什么?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说:“女人,是个相对的人。”
他的意思是,女人无法定义自身,而要通过“男人”来定义自身。
那么,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是什么?
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的故事可以给出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答案。
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是男人们梦寐以求的。
但正如李夫人所说,像汉武帝这样的男人,他爱的并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的“色相”。
假若一个男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男人,那么他势必会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化入他的骨髓。
而钩弋夫人不仅美得“沉鱼落雁”,还给年逾60的汉武帝生一个儿子,帮助他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是更完美的女人了。
但和李夫人一样,在汉武帝那里,她自身的价值一样也是不存在的。
最具色相的李夫人是汉武帝宠幸的“性对象”,而钩弋夫人则是汉武帝传宗接代的“工具”。
她们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比弗洛伊德层面的“潜意识”更深的,是“集体无意识”。
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集体无意识,而这集体无意识中,藏着很多原型。
每一个典型的人,都可以视为这个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的映现。
由此,我们可以说,李夫人和钩弋夫人即是我们文化中的女性原型。
理解了她们的故事,也就理解了女人的很多心理。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当你觉得很难理解现代女性的心理时,你不妨去想一想李夫人和钩弋夫人这些历史上的名女子的故事。
或许,你可以从那里找到一些答案。
回到那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如果,仅仅通过我做咨询的经历,则可以说:
女人,是想“抓住男人”而不得、并由此感到痛苦的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我成年的女性来访者,基本上最初都是因“婚姻恋爱”的问题而来找我。
她们当中,有近80%的人有着类似的痛苦 —— 她们最在乎的男人不在乎她们。
常常有人会说,女人是情感的动物。
所以,一旦发现爱情似乎不存在时,她们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中。
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男人也是爱情的动物。一旦发现爱情不存在时,男人的整个存在感也会受到动摇。
问题是,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理解不同,似乎可以概括成:
女人对爱情的理解,导致了男人的痛苦。
而男人想逃离这种痛苦时,就会被女人理解成“他们不爱自己”。
于是,男人会由此陷入更大的痛苦。
女人如何理解爱情?
我一位来访者的说法虽然极端一些,但非常典型,她对我说:
“丈夫对我好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天堂;他对我坏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地狱。为什么他偏偏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她说得理直气壮。
以至于那一刻,我在恍惚中以为,心理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每个人为自己的感受负责”真的不成立了。
作为咨询师,我理解她这种心理的合理性。
同时,作为男人,我也同情她的丈夫。
她对自己这个观点有多肯定,她的丈夫就会有多痛苦。
这种痛苦,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深有体会。
在一个飘雪的夜晚,82岁的托尔斯泰再也无法忍受妻子。他逃离家,逃入寒冷黑暗中。
11天后,他在一个火车站上死于肺炎,而临终前最后的要求是:不许妻子来到他的跟前。
列夫·托尔斯泰没有在他的生活中找到和平。
这种痛苦,美国总统林肯也深有体会。
他遭遇暗杀,身负重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不许妻子来看他。
我一位来访者也描述过男人的这种痛苦。
他说,他的岳父去世前,看到他岳母走进房间的一瞬间,突然激动起来,挣扎着向妻子伸出一支手,挥舞着,好像在对相处一生的妻子大喊:“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
这几个男人的这种痛苦,在我看来,都源自于他们无法很好地处理妻子的那种人生哲学 ——“我的感受由你负责,你对我好一点我就在天堂,你对我坏一点我就在地狱,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看起来,这个人生哲学似乎没什么,不就是“好一点”吗?
但这其实是要加一个定语的——“时时刻刻”。
女人一旦有了这样的信念,她的注意力就会完全放在伴侣身上,这就成了男人不能承受的沉重。
对此,法国作家蒙特朗非常反感,他因而将女人描绘成男人的噩梦。
他欣赏尼采对女人的态度:“见女人时,带上一条鞭子”。
他认为男人必须高高在上,对女人必须粗暴,否则,女人就会吃掉他们的力量。
他说,对女人来说,爱就是“吞没”。在假装“给予”的同时,必须“攫取”之。
一如托尔斯泰夫人令人战栗的呐喊 :“我以他为命,为他而活,我要求他也像我对他一样来对待我。”
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爱她的先生。我问她,你怎样爱他呢。
她说:“每当他回到家里,我必定已为他准备好了一份水果、一杯茶水和一套睡衣。甚至,连牙刷上都挤好了牙膏。”
这简直像极了托尔斯泰夫人的心声:“以他为命,为他而活”!
但假若这就是全部,那也没什么。而这位女士在聊天中也一再强调说,这就是全部,她别无所求。
但她先生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他对她说:“你不要为我做这些事。你为我做这些事时,总有期待。如果我满足不了你的期待,你就会生气。”
她恍若听不见先生的这番话。
她说:“我就是爱你,所以,我必须这样做。”
结果,她越这样做,先生越不耐烦。
我建议她试试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她这样做了。
这时他说:“这就对了,这样我很舒服。”
并且很快,他对她的不耐烦减轻了。
这个“不耐烦”,是对女人暗含的那份“我要求他也像我对他一样来对待我”的抵触。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情人、同样是著名哲学家的法国女子西蒙娜•德•波伏娃写了一部世界级的名著《第二性》,专门来探讨女性。
《第二性》书名的意思即,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男人是“the one”,女人是“the other”。
翻译过来即,男人是“主体”,女人是“他者”。
所谓“他者”,即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我们流传的萨特名言“他人即地狱”,其实意思是“他者即地狱”。
对于女性而言,因为种种原因,女性沦为了“他者”。所以,女性容易深陷于地狱中。
“他对我好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天堂,他对我坏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地狱。”
这说明,这位女子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下,将自己置于“他者”的位置上。而结果,也当真如身处“地狱”。
但是,为什么女性容易陷入“他者”的地狱中呢?
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的故事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时,事实的确是:汉武帝这样的男人在掌控着一切。
李夫人和钩弋夫人的价值,甚至生死,都系于这个男人如何对待自己。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说:一个人沦为了另一个人实现自己欲望的对象或工具,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
由此可以看到,李夫人就是汉武帝性欲与爱欲的对象,而钩弋夫人则是汉武帝传宗接代的工具。
不是她们将自己置于“他者”的位置上,是汉武帝强势地将她们置于这个地狱中。
李夫人对这一点洞若观火,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将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中。
她只给汉武帝展现自己最好的色相,而不让汉武帝看到自己的“色驰”,由此成了汉武帝梦牵魂绕的性欲与爱欲的完美对象。
钩弋夫人不能明白这一点,当汉武帝下令处死她时,她跪地哀号,而遭到汉武帝的呵斥:“快走快走,你反正是活不了的。”
据记载,她死后数天里“暴风扬尘”,就像是她的冤魂在哀号。
钩弋夫人的惨剧并非例外。
实际上,“荣其子、杀其母”是汉武帝的通例。他的妃子们一旦生了孩子,都会被他以各种名义处死。
他这样做,源自于他自己的经历。他幼时和刚上任时,曾受母亲和祖母很大的牵制。
所以,“主少母壮”并非是他在替自己的父辈或祖父辈有吕后这样的“超级专制的妈妈”而感叹,他是在为自己感叹。
由此,可以理解,他杀死钩弋夫人,看起来像是为年幼的儿子扫除障碍,但其实,是他想杀死母亲和祖母的潜意识心理的投射。
他谥号“孝武”,孝自然是针对母亲和祖母,但可以说,他对母亲和祖母表现得有多孝顺,他潜意识隐藏着的对母亲和祖母的攻击性就有多强,而这最终表现成他对妃子们的残酷逻辑 —— “荣其子杀其母”。
汉武帝的这种做法也并不孤独。在中国历史上,“荣其子杀其母”的做法相当常见。
那些史书记载的血泪故事里,女性的命运就犹如浮萍一样脆弱。
作为爱欲与性欲的对象,会有“色衰而爱驰,爱驰而恩绝”的后果,而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甚至可能会更惨烈。
李夫人对于汉武帝的意义,可以在现代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上找到很明显的对应。
男人对女人美貌的在乎,估计在每一个社会都是很主流的态度。
钩弋夫人对汉武帝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似乎不是很明显了。
可在最传统的地区,譬如潮汕和客家地区,女人还普遍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不过好在,主流的做法还是“因其子荣其母”。
但是,在这种地区,假若一个女人不能生儿子,或者很艰难才生了儿子,那么对她自己和对女儿们而言都可能会是一场噩梦。
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女人生一个是女儿,又生一个还是女儿,于是就一直生,直到生了七八个女儿后才生了一个儿子,那时,她才可以不再做“生育机器”。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将女儿送给别人是很常见的事。欧美国家到中国来收养的孩子,多数就是这种家庭生出的女儿。
最恐怖的是,生下来的女儿被虐待、甚至被残杀。
我知道在一个家庭,在接连生了几个女儿后,最后一个女儿刚一落地,就被父亲活活摔死了。
作为一个女人,假若你是出生于这样的家庭,那么,你很难不陷入到“他者”的地狱中。
在我们国家,重男轻女至少有数千年的传承了。
所谓重男轻女,也就意味着:女人的价值不在于她们自身,而在于她们对男人来说是什么。
如果她们在男人的眼里是重要的,那么她们就是有价值的;
如果她们在男人的眼里是不重要的,那么她们就是没有价值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我好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天堂,他对我坏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在地狱”,女人发出这样的感触,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于钩弋夫人来说,这直接意味着生与死。
生与死是极端的表现,大多数女性的命运不会在这种极端处游走,但她们难以免除一种痛苦 —— “被抛弃”的痛苦。
被杀死是极致的“被抛弃”,被送人则是相对轻一些但也是极致的痛苦,而女性普遍所接受的痛苦到不了这种地步,她们所遭受的痛苦,主要是忽视、冷落乃至虐待。
更要命的是,她们之所以被忽视、冷落乃至虐待,原因常常仅仅是:她们是女孩。
并且,更更要命的是,最初这样对待她们的,恰恰是自己的妈妈,而且还是生命的最早期。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首先,成年女性的生命价值被否定了,她们必须依附于男人而生存。
她们作为女性而被蔑视、被否定甚至被欺辱,这令她们讨厌自己的“女性”身份。
接着,她们有了女儿。
如果不是有很好的觉知,她们会将对自己的“女性”身份的讨厌和抵触,淋漓尽致地投射到女儿身上。
在生命的最早期,这种讨厌和抵触可能会表现为:
她们不愿意碰触女儿;
不愿意给女儿喂奶;
忽视、冷落女儿,乃至虐待她们。
媒体经常有报道说,幼小的女孩身上被插进了很多针,而这些报道有时会证实,做如此残酷的事情的,恰恰是女孩的奶奶。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奶奶的智慧没有增长,反而是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恨意逐渐增长。
这份恨意,最终会传递到幼小的女孩身上。
生命早期的这些创痛,是非常难以平复的。
托尔斯泰与林肯所遭遇的创痛是“被吞没”的创痛。这种创痛很深,但它比不上“被抛弃”的创痛。
托尔斯泰与林肯是有“自我”的。
他们的痛苦是发现,在与妻子的朝夕相处中,正在失去“自我”。他们的“自我”被妻子吞没了。
而他们的妻子是没有“自我”的。
她们所遭遇的被抛弃的痛苦,令她们很早就失去了“自我”。
并且,每当她们试着去寻找“自我”时,她们总是会碰到被抛弃的创痛。这种创痛看起来是不可修补的。
这时,她们就会去抓伴侣,而这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且是一种上瘾。
因为看起来,当自己痛苦时,男人对自己好一点,真的会有天堂的感觉,所以她们会不断去追逐这种逃避痛苦的方式。
这种做法无异于吸毒。而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拒绝做毒品。
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成为一个“主体”,女人就必须学习打破这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