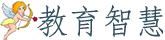程蝶衣的母亲是个妓女,而他自己演的也是妓女 —— 虞姬 —— 虽然社会地位高一些。
而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个妓女。
而他心爱的男人,也被一个妓女俘虏了。
他自己,也曾经出卖过色相,虽然可以替他辩护:那是被逼无奈。
其实,就人生而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逼迫一个人的。
程蝶衣的一生只有一个信仰:从一而终。
什么是他的这个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一”呢?
哦,我知道精神分析家们会怎么说:母亲、指头、师傅、师兄、霸王、京戏。
而这些所有东西都会凝缩 —— 是的,这是弗洛伊德《释梦》中的那个词 —— 成一个符号、一个器官、一个术语,男根(phallus)、阴茎、他者或者是身份(identity)。
母亲砍断他多出来的六指的时候,也砍断了他和母亲的纽带。
也象征地砍断了他的阴茎,我们不难听到用“指头”暗喻阴茎的俗语。
程蝶衣的命运就在于他一开始就被阉割,或者说压抑。
而他必须不断地追寻他丧失了的东西 —— 男根 —— 男性的根本所在。
他首先在自己的身上寻找,但是这种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受到阻挠。
戏班师傅告诉用殴打和酷刑告诉他:你不是男儿郎,而是女娇娥。
最有意思的是,处处维护他的师兄小石头也殴打了他,因为他的无意识总在用口误的形式呐喊: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小石头用一根烟管插进他的嘴巴,狠命搅动出血,这种举动似乎暗示着,你所寻找的男根在我这里,而不在你。
而程蝶衣似乎要一辈子接受的命运是:像那张出血的嘴巴一样,接纳、被动、违心、逆来顺受。
当然,在半生不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眼里,这种举动是性感的。
所有的人,包括袁四爷、张太监和大部分热恋程蝶衣扮演者张国荣的影迷,都只能接受作为虞姬的程蝶衣。
是的,没有什么程蝶衣,也没有什么小豆子,哪怕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这样的身份他都没有。
只有一个旦角、一个虞姬、一个舞台上的妓女在生活着。而他只有成为具备这么一个身份,才能够得到尊重、赞赏、自我和爱。
作为程蝶衣的他,一个弃子,没有任何价值,激不起任何的欲望。
所以,他不能把戏和生活分开,一旦分开,他将要丧失身份,这预示着自我的死亡。
他怎么可能 —— 不能说“可以”,这个词对他太沉重 —— 成为一个男人呢?怎么可能具有男根呢?
他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 —— 做一个永恒的姘妇(concubine),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
文革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是什么东西了,只剩一张皮!
他接受了这种安排。
不过,他接着说:“可是 —— ”
这个“可是”表明,探寻男根的历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你楚霸王也下跪了,你说这京戏能不亡吗?
在自己身上找不到的,他需要找别人身上发现。然后,把自己和这个别人融为一体。
这个别人当然是师兄 —— 霸王,以及作为这种投射性探寻的语境 —— 京剧。
所以他发出邀请,要和师兄一辈子演《霸王别姬》,少一个月、一天、一分钟都不算一辈子。
这个邀请的含义是:让我成为你,让你成为我,同生共死。
这个霸王应该是有骨气的、临死不屈的,和他共赴死亡的盛宴。
可是段小楼提醒他:那是戏!这是疯魔。
是,这是一个残酷的游戏、一个注定破灭的梦想。
程蝶衣看到,原来一直保护他的师兄背叛了他、一直视为亲子的徒弟背叛了他。而且,不止一次。
没有什么霸王,没有什么虞姬,没有什么从一而终,只有琐碎、卑微的生命和聊以自慰的梦想 —— 京剧。
他受骗了。他说,我也要揭发,揭发才子佳人,揭发断壁残垣。
他要揭发他的梦,他的幻想,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是的,没有他幻想中的无所不能的好妈妈、好爸爸、好师兄、好男人,这一切都是幻想。
他说,你们都骗我。
哦,其实是自己在骗自己。
他写信给那个不存在母亲,把生活描述成一片美好。而这,不过是幻觉,和吸大烟产生的幻觉没什么不同。
或者我们可以说,包括所有人孜孜以求的男根,也是一种幻觉,它只能够在幻想的世界存在。
追寻男根的过程,终点矗立着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实际上没有男根。”
此路不通,没有阴茎、没有男根、也没有身份。
从一而终,可是哪里有个“一”让人可“从”呢?
程蝶衣,只有死路一条。
死之前,口误再次出现:“我本是男儿郎。”
对别人所有的幻想、投射都收回来了,他只能把男性的身份还给自己。
而这个执著的男人、这个小豆子、这个妓女的弃子必须杀死他自我的幻像 —— 虞姬。
这个幻象附着于他的肉身。
“虞姬总有一死啊。”那爷在怂恿把小豆子送给张太监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一切。
我们无法想象,在《霸王别姬》中,虞姬和乌骓马想抱而泣,可是霸王却去投诚了。
霸王,气盖世,有气节,慨然赴死。
可那是戏,不是生活。
生活是,揭发后 —— 我们应该说揭发梦想后吗 —— 虞姬和菊仙凄然相对,而霸王不知在什么地方?
程蝶衣和菊仙,究竟谁是段小楼的乌骓马,谁是虞姬?
菊仙对爱情也有一个梦想,一个拯救他的男人,一个英雄,一个不离不弃的丈夫。
她能够放弃尊严、放弃面子、放弃喝彩,顺应时势。
但是这个梦她不能放弃。
她和段小楼结婚的时候,这个梦似乎实现过。
可是,当段小楼对造反派承认,她就是个妓女,我不爱她的时候,这个梦破了。
自杀的时候,她把现场布置成结婚的情景,通过死亡,她和自己的梦想合而为一。
她也在段小楼身上追寻霸王的影子。
直到最后,不知道她是否明白,这个霸王在她心里,从来就只是她自己的一部分。
她生存的底线是:从一而终。这个“一”对她来说,似乎就是没有背叛的爱情。
可是没有背叛,爱情也就失去了价值。
或者说,背叛是根本的,爱情是用来压抑背叛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具有霸王气质 —— 执著、从一而终、坚定的理想主义精神 —— 的人恰恰是菊仙和程蝶衣。
菊仙和程蝶衣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潜意识中彼此爱着对方。
当然,这有一种母子恋的意味,程蝶衣戒毒时,呼唤母亲,和她拥抱,已经提示了这一点。
《别了,我的姘妇》是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farewell to my concubine !
绝妙的翻译,这隐含了一个事实,这里面没有霸王。
段小楼实际上是最可悲的人物,没有他的位置。
程蝶衣有他坚定的信仰、有他的身份。
菊仙也有。
而段小楼,什么都没有。
程蝶衣,不是什么东西,只剩一张皮。
而他,连一张皮都没有。
相比起来,菊仙和程蝶衣是幸福的,他们能够自杀,就说明他们还有一个身份、有一个自我。
而段小楼,连自我都没有、连身份都没有,要自杀也无从下手。
他要孝顺师傅,要照管师弟,要保证家庭的安稳,而且,还要与时俱进。
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收敛锋芒,不能为所欲为。
可是,他不能脆弱、不能流泪、也不能临阵逃脱。他还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救助弱小,要有点霸道,要不畏权贵,要不为五斗米折腰。
人们抛给他一个理想自我,霸王,供他认同。
这个理想,离他太远。
他很软弱、无能。
他自身难保,要靠师弟救命,何谈保护他人?
段小楼只有一个办法应付这些压力:以头撞砖。
自己攻击自己。从而避免别人的攻击。
可在文革的时候,就连这个方法都不管用了。
他始终不能成为霸王。因为他必须生存,而不能概然赴死。
霸王,向来是死人的专利。
在这个坚定的霸王,这个神性自我的照耀下,段小楼的生活越发显得猥琐和狼狈。
只有妓女和赌博,能让他暂且忘记自我。
可是这也无效,必须先有一个自我,才能忘我。
可要是连自我都没有呢?
哪怕一个虚假的自我,如程蝶衣的。
有的只是充满矛盾的、无法实现的几个自我理想 —— 孝顺懂事、少年老成的大师兄、演技精湛的戏子、除危济困的侠客、赚钱顾家的好男人。
所以,和师傅在一起的时候他让自己来满足师傅;和师弟在一起,他用自己来满足师弟;和老婆在一起,他又用自己来满足老婆;而造反派来了,他又用自己来满足造反派。
自我,包括其中的价值、尊严、爱,都是一个随时可以更改、可以替换、可以出租、可以赠送、可以售卖的东西。
只有一次,他拒绝了袁四爷的邀请,那是因为,袁四爷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欲望。
而他和伤兵争斗,也不是为了自我,而是为了程蝶衣。
任何人对他的欲望,哪怕是通过他来寄托自己对自我理想的欲望,他都无法拒绝。他必须抓住,从而欺骗自己:哦,我还是有些价值的。
尽管这是狐假虎威、尸位素餐。
段小楼不断地对程蝶衣强调:现实,现实,现实!
对他来说,有什么是现实的呢?
花酒?女人?戏?同胞之情?
正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现实可言,他才要拼命抓住现实。
而他拼命要抓住的东西,统统离他而去。
一个孤独的人。
比自杀的项羽更加孤独,项羽的身边有忠诚的战马和情人,心中有江东父老。
而来到段小楼身边的一切,都是相应那个霸王的幻影而来,在揭发之后,一切又潮水般退去。
他只有孤零零地呆着舞台上,畏缩在霸王的五彩的戏服和脸谱之后。
段小楼,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中国男人。
他们生存着,只能生存着。
他们 —— 或者说,我们?—— 没有爱、没有尊严、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 —— 只有虚无飘渺的面子。
而这个面子,是其他人的。
永远都不属于我。
面子比男根更加虚无。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男根存在幻想的世界中,在死亡中可能与之相遇。
而面子,它告诉你:我不是幻想,也不存在于现实中,我是很真实的,但你永远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寄居。
面子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没人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没有人见过他,但所有人都知道他。
是的,段小楼从来没爱过任何人,包括他自己。
他的妻子菊仙,也知道必须在整个戏班在场的情况下,隐讳地向他求婚。
为了面子,为了大家的高兴,为了戏班同行的恻隐之心,段小楼会毫不犹豫的和菊仙结婚。
这不是他自己在结婚,就像一位咨询者所说:“我是为了别人结婚的。”
段小楼和菊仙的关系是一种“姘”的关系。
这种关系中,没有一个处在正确位置上的男人,也没有一个处在正确位置的女人。
只有拼凑、合并、和暧昧的生拉硬扯、欲语还休。
确切的说,段小楼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姘”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作为一个主体存在,而只是迎合、容纳、磨平自己的头角去适应别人。
他想要变成别人的一个部分,从而找到自己所在。
但是最后他发觉,在他努力生存下来的过程中,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存在。
难道这不是最大的玩笑吗?
一个努力追寻生活的人,却因为追寻生活本身丧失了生活。
段小楼,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妓女。和那爷一模一样。
他们不可能从一而终,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包括“一”。
菊仙和程蝶衣的生命尽头,会有个声音告诉他们:“你追寻的东西是个空想。”
但是,并没有否认这种追寻的轨迹。
而段小楼道路的尽头,那个声音是,“你根本没有走过任何道路,也根本没有追寻过任何东西。虽然你以为你追寻过。”
有人说,心理健康的标准是适应社会。
那么,段小楼应该是最健康的,还有那个经理人那爷。
他们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的心理健康,自我功能良好,没有什么内心冲突,也没有太多的哀愁。
我们从来不会愚蠢到要追求从一而终,总是左右逢源的。
我们从来不会愚蠢到要追求从一而终,总是左右逢源的。
作者|李孟潮,精神分析家,心理咨询师,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临床督导。文章出自《在电影院遇见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