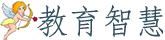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尽管过去的中国文学如何优美,如果我们坐井观天,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我们就难免对本国文学也不能尽量了解欣赏。美丑起于比较,比较资料不够,结论就难正确。纯正的文学趣味起于深广的观照,不能见得广,就不能见得深。现在还有一批人盲目地颂扬中国文学,盲目地鄙弃外国文学,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个大障碍。我们承认中国文学有很多优点,但是不敢承认文学所可有的优点都为中国文学所具备。单拿戏剧小说来说,我们的成就比起西方的实在是很幼稚。至于诗,我们也只在短诗方面擅长,长诗根本就没有。再谈到文学研究,没有一个重要的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详细而且精确的传记可参考,没有一部重要作品曾经被人作过有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没有一部完整而有见解的文学史,除《文心雕龙》以外,没有一部有哲学观点或科学方法的文学理论书籍。我们以往偏在注疏评点上做功夫,不失之支离破碎,便失之陈腐浅陋。我们需要放宽眼界,多吸收一点新的力量,让我们感发兴起。最好我们学文学的人都能精通一两中外国文,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名著。为多数人设想,这一层或不易办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们必须作大规模的有系统的翻译。
谈到翻译这并不是一件易事,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这不仅要懂文学,还须看懂文学后面的情理韵味。一般人说,学外国文只要有阅读的能力就够了,仿佛以为这并不很难。其实阅读就是一个难关。许多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的书仍不免错误百出,足见他们对于外国文阅读的能力还不够。我们常易过于自信,取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从头读到尾,便满以为自己完全了解。可是到动手译它时,便发现许多自以为了解的地方还没有了解或是误解。迅速的阅读使我们无形中自己欺骗自己。因此,翻译是学习外国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训练我们细心,增加我们对于语文的敏感,使我们透彻地了解原文,文学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语文的运用,对语文不肯仔细推敲斟酌,只抱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就只能得到一个粗枝大叶,决不能了解文学作品的精妙。
阅读已是一个难关,翻译在这上面又加上一个更大的难关,就是找恰当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阅读只要精通西文,翻译于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许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译的书籍往往比原文还更难懂,这就未免失去翻译的意义。
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欣合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稍有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极难的事。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们必求尽量符合这个理想,在可能范围之内不应该疏忽苟且。
“信”最难,原因甚多。头一层是字义难彻底了解。字有种种不同方式的意义,一般人翻字典看书译书,大半只看到字的一种意义,可以叫做直指的或字典的意义(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比如指“火”的实物那一个名谓字,在中西各国文字虽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却是同一实物,这就是古字典上所规定的。这种文字最基本的意义,最普遍也最粗浅。它最普遍,因为任何人对于它有大致相同的了解。它也最粗浅,因为它用得太久,好比旧铜钱,磨得光滑破烂,虽然还可用来在市场上打交易,事实上已没有一点个性。在文学作品里,每个字须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生命。所以文学家或是避免熟烂的字,或是虽用它而却设法灌输一种新生命给它。一个字所结的邻家不同,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和“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两诗中同有“江南”,而前诗的“江南”含有惜别的凄凉意味,后诗的“江南”却含有风光清丽的意味。其次,一个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杜甫的名句:“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棲老凤凰枝”,有人疑这话不通,说应改为“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棲老碧梧枝”。其实这两种说法意义本不相同。杜句着重点在“香稻”和“碧梧”(香稻是鹦鹉啄残的那一粒,碧梧是凤凰棲老的那一枝),改句着重点在“鹦鹉”和“凤凰”(鹦鹉啄残了香稻粒,凤凰棲老了碧梧枝),杜甫也并非倒装出奇,他当时所咏的主体原是香稻碧梧,而不是鹦鹉凤凰。这种依邻伴不同和位置不同而得的意义在文学上最为重要,可以叫做上下文决定的意义(contexual meaning)。这种意义在字典中不一定寻得出,我们必须玩索上下文才能明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学修养而又粗心,对于文字的这一种意义也难懂得透彻。
此外文字还有另一种意义,每个字在一国语文中都有很长久的历史,在历史过程中,它和许多事物情境发生联想,和那一国的人民生活状态打成一片,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氛围。各国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状态不同,同指一事物的字所引起的联想和所打动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firesea,Roland,castle,sport,shepherd,nightingale,rose之类字对于英国人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和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大有分别。它们对于英国人意义较为丰富。同理,中文中“风”、“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隐逸”、“礼”、“阴阳”之类字对于我们所引起的联想和情趣也决不是西方人所能完全了解的。这可以叫做“联想的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它带有特殊的情感的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也就茫然,尤其在翻译时,这一种字义最不易应付。有时根本没有相当的字,比如外国文中没有一个字恰当于我们的“礼”,中文没有一个字恰当于英文的“gentleman”。有时表面上虽有相当的字,而这字在两国文字中情感氛围,联想不同。比如我们尽管以“海”译“sea”或是以“willow”译“柳”,所译的只是字典的直指的意义,“sea”字在英文中,“柳”字在中文中的特殊情感氛围则无从译出。
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其次就是声音美。字有音有义,一般人把音义分作两件事,以为它们各不相关。在近代西方,诗应重音抑应重义的问题争论得很剧烈。“纯诗”派以为意义打动理想,声音直接打动感官,诗应该逼近音乐,力求声音和美,至于意义则无关宏旨。反对这一说的人则以为诗根本不是音乐,我们决不能为声音而牺牲意义。其实这种争执起于误解语言的性质。语言都必有意义,而语言的声音不同,效果不同,则意义就不免有分别。换句话说,声音多少可以影响意义。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说,“他又来了”和“他来了又去了”两句话中都用“又”字,因为腔调着重点不同,上句的“又”字和下句的“又”字在意义上就微有区别。做诗填词的人都知道一个字的平仄不同,开齐合撮不同,发音的器官不同,在效果上往往悬殊很大。散文对于声音虽没有诗讲究得那么精微,却也不能抹杀。中西文字在声音上悬殊很大,最显著的是中文有,而西文没有四声的分别,中文字尽单音,西文字多复音;中文多谐声字,西文少谐声字。因此,无论是以中文译西文或是以西文译中文,遇着声音上的微妙处,我们都不免束手无策。原文句子的声音很幽美,译文常不免佶屈聱牙;原文意味深长,译文常不免索然无味。文字传神,大半要靠声音节奏。声音节奏是情感风趣最直接的表现。对于文学作品无论是阅读或是翻译,如果没有抓住它的声音节奏,就不免把它的精华完全失去。但是抓住声音节奏是一件极难的事。
以上是文字的四种最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第一种是“历史沿革的意义”(historic meaning)。字有历史,即有生长变迁。中国文言和白话在用字上分别很大,阅读古书需要特殊的训练,西文因为语文接近,文字变迁得更快。四百年前(略相当于晚明)的文字已古奥不易读,就是十八世纪的文字距今虽只一百余年,如果完全用现行字义去解,也往往陷于误谬。西文字典学比较发达,某字从某时代变更意义或新起一意义。常有例证可考。如果对文字沿革略有基础而又肯勤翻详载字源的字典,这一层困难就可以免除。许多译者在这方面不注意,所以翻译较古的书常发生错误。
其次,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欢喜开一点玩笑,耍一点花枪。离奇的比譬可以使一个字的引申义与原义貌不相关,某一行业的隐语可以变成各阶级的普通话,文字游戏可以使两个本不相关而只有一点可笑的类似点的字凑合在一起,一种偶然的使用可以变成一个典故,如此等类的情境所造成的文字的特殊意义可以叫做“习惯语的意义”(idiomatic meaning)。普通所谓“土语”(slang)也可以纳于这一类。这一类字义对于初学是一个大难关。了解既不易,翻译更难。英文的习惯语和土语勉强用英文来解释,还不免失去原有的意味;如果用中文来译,除非是有恰巧相当的陈语,意味更索然了。
从事翻译者必须明了文字意义有以上几种分别,遇到一部作品,须揣摩那里所用的文字是否有特殊的时代、区域或阶级上的习惯,特殊的联想和情感氛围,上下文所烘托成的特殊“阴影”(nuance),要把它们所有的可能的意义都咀嚼出来,然后才算透懂那部作品,这是易事,它需要很长久的文字训练和文学修养。看书和译书都必有勤翻字典的习惯,可是根底不够的人完全信任字典,也难免误事,他只能得一知半解,文字的精妙处实无从领会。一般英汉字典尤其不可靠,因为编译者大半并不精通外国文,有时转抄日译,以讹传讹。普通这一类字典每页上难免有几个错误或不精确处。单举一两个极普通的字来说,在中国一般学生心里,pride只是“骄傲”,envy只是“妒忌”,satisfactory只是“满意”。其实“骄傲”和“妒忌”在中文里含义都不很好,而pride“尊荣心”和envy“欣羡”在英文里却有很好的意思,至于satisfactory所“满”的并不一定是“意”,通常只应译为“圆满”。这种不正确的知解都是中了坏字典的毒。
上文只就文字的意义来说,困难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语句的组织,又可发现其他更大的困难。拿中文和西文来比较,语句组织上的悬殊很大。先说文法。中文也并非没有文法,只是中文的弹性比较大,许多虚字可用可不用,字与词的位置有时可随意颠倒没有西文法那么谨严。因此,意思有时不免含糊,虽然它可以做得很简练。其次,中文少用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特点在简单明了,但是没有西文那样能随情思曲折、变化而现出轻重疾徐,有时不免失之松散平滑。总之,中文以简练直截见长,西文以繁复绵密见长,西文一长句所含包的意思用中文来表达,往往需要几个单句才行。这对于阅读比较费力。初学西文这看见一长句中包含许多短句或子句,一意未完又插入另一意,一个曲折之后又一个曲折,不免觉得置身五里雾中,一切都朦胧幻变,捉摸不住。其实西文语句组织尽管如何繁复曲折,文法必定有线索可寻,把文法一分析,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中国人学西文必须熟悉文法,常作分析句子的练习,使一字一句在文法上都有着落,意义就自然醒豁了。这并非难事,只要下过一两年切实仔细的工夫就可以办到。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这两种错误第一种比较难免,因为文字意义的彻底了解需要长久的深广的修养,多读书,多写作,多思考,才可以达到;至于语句文法组织有一种规律可循,只要找一部较可靠的文法把它懂透记熟,一切就可迎刃而解。所以翻译在文法组织上的错误是不可原恕的,但是最常见的错误也起于文法上的忽略。
语句文法组织的难倒不在了解而在翻译,在以简单的中文语句来译繁复的西文语句。这种困难的原因很多,姑举几个实例来说明:
1.But my pride was soon humbled, and a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over my mind, by the idea that I had taken an everlasting leave of an old and agreeable companion; and that,whatsoever might be the future date of my History, the life of the historian must be short and precarious. -E. Gibbon
2.This is why those periods have been so exceptional in history in which men who differed from the holders of power have been permitted, in an atmosphere of reasoned calm,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insight they claim. -H. Laski
3.All the loneliness of humanity amid hostile forces is concentrated upon the individual soul, which must struggle alone, with what of courage it can command, against the whole weight of a universe that cares nothing for its hopes and fears. -B. Russell
这三句文字并不算很难,我叫学生试译,意思译对的不多,译文顺畅可读的更少。我自己试译,译文读起来也不很顺口,至于原文的风味更减色不少:
(一)但是我的自豪不久就降下去,一阵清愁在(我的)心头展开,想到我已经和一个愉快的老伴侣告永别;并且想到将来我的史书流传的日子无论多么久,作史者的生命却是短促而渺茫的。
(二)因此,人们和掌权者持异见时,还被允许(可以)在心平气和的空气中证明他们所自以为有的真知灼见是对的,这种时会在历史上很不多见。
(三)人类在各种对敌的(自然)势力之中所感受的寂寞都集中在各个人的心灵上,这各种人的心灵不得不凭它以能鼓起的勇气,孤独地奋斗,去撑持宇宙的全副重压,那宇宙对于它(各个人的心灵)的希冀和恐惧是漠不关心的。
我们感觉的困难有几种。头一种是复句。中文里不常用关系代名词和连接词(relative pronouns and conjunctions)如which,that,whose,where,when之类,所以复句少。我们遇着用关系代名词和连接词很多的复句,翻译起来就感到棘手。比如第一例的by the idea that and that第二例的why,in which,who第三例的which,that都很难直译。第一例只好把by the idea that译成“想到”。第三例why前后文本是一气,译文只好把它译成有停顿的子句“因此”,in which一个插句只好和主句those periods……分开,把主句移置于全句尾。这样译,可以避免冗长笨重的句子如: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时期在历史上很是例外,当其中人们和掌权者持异见还被允许……
但是第三例中两个代名词which和that就无法直译。Which本是代前面的“这各个人的心灵”,中文没有相当的代名词,只好把“这各个人的心灵”复述一遍,that代前面的“宇宙”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原文一个复句便变成三个单句。它的绵密组织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因此就不能保存了。总之关系代名词和连接词所造成的复句在西文里很自然,在中文里很不自然,译西文复句时常须把它化成单句,虽然略可传达原文的意思,却难保存原文的风味。如果不把它化成单句,读起来就很不顺口,意思既暧昧,风味更不能保存。
其次,我感觉的困难是被动语气(passive voice)。被动语气在西文里用得很多,在中文里却不常见,依中文习惯,在应该用被动语气时,我们仍用主动语气。例如:
他挨打了(他被打了)。
秘密让人发现了(秘密被发现了)。
房子给火烧了(房子被火烧了)。
碗打破了(碗被打破了)。
他不为人所了解(他不被了解)。
孟子不列于学官(孟子不被列于学官)。
如此等例不可胜举。在翻译时,如果遇到被动语气,就很难保存。例如:
It is said that his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一句英文,依被动口气,应该译为:
那是被说过,他的书已被发行了。
但是依中文习惯,它应该译为:
据说,他的书已发行了。
上面引的Gibbon,“自传”里一段文字只是一个用被动语气的长句,可分析为下式:
My pride was humbled by the idea that…
a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and that…
如果勉强保持原文被动语气,那就成为:
但是我的自豪不久就被我已知一个愉快的老伴侣永别那一个念头,和我的史书将来流传的日子无论多么久,而作史者的生命却是短促而渺茫的那一个念头所降伏下去了;而且一阵清愁也被这两个念头散布在我的心头。
一般初学者大半这样生吞活剥地翻译,但是这句话是多么笨重!为求适合中文习惯使语气顺畅起见,被动语气改译为主动语气较为方便。但是西文的被动语气有它的委婉曲折,译为主动语气,就难保存。比如上文所引的Laski一句中的Men…have been permitted依英文被动语气应译为“人们被允许”;依中文习惯应译为“人们可以”;“被允许”和“可以”究竟有一点差别。
第三,原文和译文在繁简上有分别,有时原文简而明;有时原文字多才合文法。译文须省略一些字才简练。比如第一例Whatsoever might be the future date of my History直译应为“无论我的史书的将来的日子是怎样”,意思就不明白,我们必须加字译为“我的史书将来流传的日子无论多么久”。第二例“人们和掌权者持异见时还被允许……”加了“时”字文气才顺,加了“还”字语气才足。第三例struggle alone…against the whole weight of a universe直译应为“孤独地向宇宙的全副重压奋斗”,但是意思不如“孤独地奋斗,去撑持(或抵挡)宇宙的全副重压”那么醒豁。至于虚字的省略是很容易见出的,第一例and a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over my mind中and(而且)和my(我的)都可以不译。中文用虚字比西文较少,这是文字习惯,可省略的就不必要。
这是关于语句组织的几大困难。此外像词句的位置,骈散长短的分配,中西文也往往不同,翻译时我们也须费心斟酌。在这里我们可以趁便略谈直译和意译的争执。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译”偏重对于原文的忠实,“意译”偏重译文语气的顺畅。哪一种是最妥当的译法,人们争执得很厉害。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忠实的翻译必定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感情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不过同时我们也要顾到中西文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仍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并无害于“直”。总之,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一般人所谓直译有时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就是中西文都不很精通的翻译者,不能融会中西文的语句组织,又不肯细心推敲,西文某种说法恰当于中文某种说法,一面翻字典,一面看原文,用生吞活剥的办法,勉强照西文字面顺次译下去,结果译文既不通顺,又不能达原文的意思。许多这一类的译品读起来佶屈聱牙,远比读原文困难,读者费很大的气力还抓不住一段文章的意思。严格地说,这并不能算是直译。
一般人所谓意译也有时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就是不求精确,只粗枝大叶地摘取原文大意,有时原文不易了解或不易翻译处,便索性把它删去,有时原文须加解释意思才醒豁处,便硬加一些话进去。林琴南是这派意译的代表。他本不通西文,只听旁人讲解原文大意,便用唐人小说体的古文敷衍成一部译品。他的努力不无可钦佩处,可是他是一个最不忠实的译者。从他的译文中见不出原文的风格。较早的佛典翻译如《佛教遗经》和《四十二章经》之类,读起来好像中国著述,思想和文章风格都很像是从印度来的。英国人译布瓦洛(Boileau)的《诗艺》,遇着原文所举的法国文学例证,都改用英国文学例证代替。英美人翻译中国诗常随意增加原文所没有的话,以求强合音律。这些都不足为训,只是“乱译”。
提起“改译”,人们都会联想到英文Fitzgerald所译的波斯诗人奥马康颜的《劝酒行》。据说这诗的译文比原文还好,假如这样,那便不是翻译而是创作。译者只是从原诗得到一种灵感,根据它的大意,而自己创作一首诗。近来我国人译西方戏剧,也有采用这种办法的。我们对于这一类成功尝试不必反对,不过从翻译的立场说,我们还是要求对原文尽量的忠实。纵非“改译”,好的翻译仍是一种创作。因为文学作品以语文表达情感思想,情感思想的佳妙处必从语文见出。作者须费一番苦心才能使思想情感凝定于语文,语文妥帖了,作品才算成就。译者也必须经过同样的过程。第一步须设身处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窍,和他同样感,同样想,同样地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于语文。所不同者作者是用他的本国语文去凝定他的情感思想,而译者除着了解欣赏这情感思想[的语文的融贯体之外,还要把它移植于另一国语文。使所用的另一国语文和那情感思想]融成一个新的作品。因为这个缘故,翻译笔自著较难;也因为这个缘故,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