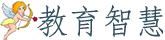四月中旬的下午,诗人幽泉与他的爱妻燕倩同坐在廊下,他手里拿着一本《词选》有意无心的翻看,她低头绣一张将近完工的窗帘子。
廊下挂了一个鸟笼,里头一只白鸽正仰头望着蔚蓝的天空尽力歌唱,好象代表它的主人送迎碧天上来往的白云。西窗前一架紫藤萝开了几穗花浸在阳光里吐出甜醉的芬香;温和的风时时载送这鸟语花香,妆点这艳阳天气。“哦——呵——我全身骨头都给这春风吹软了。”幽泉打了一个呵欠,一举手把书抛了,随着伸一伸腰,仰头枕在藤椅靠背上。他用手搓着眼说道:“燕倩,你不觉困吗?这样天气难为你还能拿着针做活。”燕倩抬头望了他一眼,微微笑答:“谁不觉得困,这样的天气!我方才迷迷糊糊的绣错了一块花瓣,这会子又得拆了重绣。”
“别绣了吧。咱们一会儿到那里走走去,这样天气那能做工呢?”幽泉枕着他自己的手,两脚搭在栏杆上,身子在椅上直挺挺的躺着。
“你今天四点钟不是已经有了约会了吗?那能出去逛?我今天打算把这帘子做完了。”
燕倩换了条花线,依旧低头刺绣。
“我呀,对了,我差些忘了今天的约会。真讨厌,这样天不能出去玩玩,反到去坐下议论那不相干的问题,真倒霉!”幽泉说到这里,咳了一声,发泄发泄他心中的闷气。接着他问:“已经四月了,再不看花,今年的春天又白过去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那里看看花去。”“明天早上我又不行!不是张太太、王太太和李小姐她们都定了明天午前来吗?他们来了两次,我都不在家,这回不好意思不在家了。”她抬眼看见幽泉很失意的样子,接下她问:“你明天见不见她们?不高兴见时,可以找朋友出去逛逛?”幽泉从椅上坐起来用手扳着后脑骨说:“老实说,你不要怪我话直,你娘认识那些太太们,我都不要见的。这样美丽风光去听她们讲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厉害,媳妇大胆,那些话,真个把人弄得头痛死了。我不打算见她们,可是找对劲的朋友玩去,有谁呢?仲云他们几个都到山上过春假了。找谁呢?没有人,明天只好躲在书房里睡半天吧!”他说完重重的呼了口气,眼直直的对着墙,唠叨起来。
“这年头真没过头,一个年青青的人,简直拘束成件机器似的,一定时候起来,一定时候吃饭,又一定时候工作;这还不算,还得你天天见不相干的人,听不爱听的话,哼,有时你还得死板板的坐下陪不相识的人吃饭。哎呀,真个把人闷死了!那怪我近来一首诗都写不出来呢!”他愈说愈觉得自己可怜,眼睛都有些发潮了,但他没有流泪,只是仰起脸望着天。
燕倩放下针线问他:“方才你多吃了半碗饭,一定饱的不好受,沏杯柠檬茶给你喝,好罢?”幽泉点点头。燕倩便去了。他还在双手托着后脑勺,哼着:“良辰美景奈何天,”“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晚上月出时,幽泉收到一封怪信,字迹极柔媚,言词很藻丽。语气很恭谨:
幽泉先生:请你不要想我们是素不相识的,实在我们在两年前就彼此认识了,我的脑府里所藏的卷册都是你的诗文,那又是时时能谐调我枯槁心灵的妙乐。在烂漫晨霞底下,趁着清明的朝气,我愿自承一切。我在两年前只是高墙根下的一根枯瘁小草。别说和蔼的日光及滋润的甘雨,是见不着的,就是温柔的东风亦不肯在墙畔经过呢。我过着那沉闷黯淡的日子不知有多久。好容易才遇到一个仁慈体物的园丁把我移在满阳光的大地,时时受东风的吹嘘,清泉的灌溉。于是我才有了生气,长出碧翠的叶子,一年几次,居然开出有颜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与众卉争一份旖旎的韶光。幽泉先生,你是这小草的园丁,你给它生命,你给它颜色(这也是它的美丽的灵魂)。
近来我被温醉的东风薰得枝叶酥软起来,非常困惫。我又被鸟歌蝶舞的引诱,觉得常常立在庭园中究竟没有享着山花一样的清福,未免心中不自在。现在我发生奢望,我想变成一只黄鸟或蝴蝶飞到郊外,任我歌唱,任我跳舞,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灵魂的人。
奢望终是奢望吗?不一定罢?我定于明日朝阳遍暖大地时,飞到西郊“花之寺”的碧桃树下。那里春花寂寂争研,境地幽绝。盼望活我的匠人去看了他自己的成绩怎样。
我的名姓不必写了,我日夕在大自然里道我的赞美,道我的感恩。我不能不爱你,但我不敢说爱你。我只是爱你。我的爱是不望报酬的爱,酬报不了的爱。
我敢对着荣耀清洁的阳光起誓,我永远不敢,且不希望,我们能成比现在关系更密切的人。只要你容许我的灵魂驻在你那里,我便十分满足了。四月十六日
“这女子倒也怪有意思的!”
幽泉说完望了望窗外无人来,拿起信重看。“她也会说,她是小草,我是她的匠人,给它生命”顺手拿起信封再细看。
“字也不坏呵!人不知怎样?家住在菊花巷;好秀气的地名。”“她‘在朝阳遍暖大地时’到郊外‘花之寺’;‘碧桃树下’,好美丽的地方!我去?燕倩知道怎行呢?可是她已经明说我们不过文字之交而已,她知道也不会怎样吧!去一次看看又何妨呢?她不会怎样的!”
他拿着信自己商量了好一会子,到底他决定会看看,他说:“一定去看看,人生能有几回做到奇美的梦。她素来明白我的,必不会为这小事生气,文字之交,有什么不行?奇美的梦,做一次。”临睡时幽泉对燕倩说他精神枯闷的慌,明天清早他要到城外看看山光草色,换换空气,他夫人也赞成他出去走走。第二天太阳还没出,幽泉便起床,匆匆忙忙漱洗了,走到镜台梳梳前短发。燕倩说他发太干了倒了些擦发香水,将发平分两边,梳平服了。他照着镜子,自看还算是一个顾影少年。不觉望了望他的夫人,见她正在笑吟吟的看着他,他脸上微微红了。早餐匆匆用过,他微笑地出了大门,坐了一部洋车乘着清和的晓风出了西直门,太阳已经满地了。
“这是‘朝阳遍暖大地’了吧?她也?”他一路想着,心里不知是喜是愁,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他觉得一生里有过几次这样情况。最记得的一次就是向燕倩求婚那一天。他想到此忽地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好象自己误走入“闲人止步”的地方,不用人呵斥已经全身不自在了。他想了又想,两次话已经溜到唇边叫车夫拉自己回家,但同时脑府中又现出“她的甘泉,给她美丽的灵魂”的字样来,脸上不觉就有点烘烘热起来。
车子穿过田庄,墓园,草屋,泥垣,及黄土深道。他坠落在沉思中,只由着车子向前走。忽地觉到车子走的太慢了,半天还不到。好容易穿出小径,打听出花之寺在西边庄子不远的地方。
西山隐隐约约露出峰峦林木寺院来,朝雾笼住山脚,很有宋元名画的风格,但他今天似乎看不见这好景。
“老爷,前边的大庙,就是花之寺了,到前边下车吗?”拉车的已经满脖子流汗,小褂的背部也湿透了。
“到那庙的大门下车吧。”他急答说。洋车还距离庙门有三丈来远,他便下了车走进庙门。砖铺的院子,砖缝里满生乱草,正殿两旁的藏经阁已经被人抽去阁顶上许多瓦片,酱红墙的灰已成片的掉下了。院内人影都没有一个,花树也没有,只有墙脚下一株被人砍去大干只留一根小干的海棠,高高的发了二三剪长枝,伸出墙头,迎着日光开几球粉红的花。
“花之寺只有这一棵可怜的花树吗?”他惘惘的望着这枝海棠。一会儿西墙外有公鸡叫的声音。他急急走向西墙,进了一个小房门。原来是一个大菜园,种的不少蔬菜。一个老头儿蹲着拔去菜里夹着新出杂草,有七八个肥大的鸡正争食撒在地上的高粱粒子。
靠南墙有五六棵二丈多高的桃杏海棠花树,虽然大干子也砍掉,但是从树根伸出的枝干,也有一丈多高了。桃杏已经开过花,长了叶子,只有半开的海棠花还带些春色。幽泉一心记挂着“碧桃树下”,无心看玩菜园残褪的春光。他招呼那老人:“借光您哪,您庙里有一棵大碧桃树吗?”
那老头儿抬头尖蒙着眼皱着眉的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才慢吞吞指着墙边桃杏树答道:“这就是庙里的桃树。”“我打听的是碧桃树,不是桃树。”幽泉重述一遍。老头儿张口望了他一回,摇摇头说:“你要劈这桃树可不行哪。前年西庄子的花儿匠来,他说要劈一两枝小桃树去接干枝梅。说明劈完给回我五吊钱,末了只给了两吊,还把大枝子劈走了。”
幽泉知道这老头儿耳目不灵了,也不耐烦听他多唠叨。闷闷的走出西院门还听见老人唠叨“劈桃树,劈了不给钱,哼,劈。”
幽泉在大院里张望了一会儿,忽然望见后殿后面似乎有亭园。他连忙走进,后面果然还不失望:有一个破到不遮风日的草亭,几堆假山石,石旁有一棵满了叶子的杏树。一棵白碧桃树正开着洁净妒雪的花,阳光照处,有几群小蝴蝶绕着飞。树底下短短的野草长满了。“这不是碧桃树吗?人在那里?”他直了眼对住桃树想:“她还没到吧,从城里来,不近呢。我在这里等她。”他拂了拂石上泥土坐在花树底下。他浑身不舒服的足足过了两点钟,乌鸦麻雀的飞来飞去动作的响声,他都要站起来心里扑扑乱跳着的望一下,还跑到山门口张望了几回,只见他的车夫张着大嘴呼呼的把头躺在车箱上熟睡,余外连狗影都看不见。他忽然看见自己的影子已经正了。已是午时,心下焦急懊丧起来,犹疑道:“莫非我被人玩弄了?谁开这样玩笑?写这封信,谁?”他走进大院前忆到《西厢记》的零断句子:
“日午当窗塔影圆,春光在眼前,玉人不见。”“再过一会我该回去了。她是不来了?咳,白做了一早上的梦!”
他深深叹了口气。“也不冤枉,到底逛到了一个有名的花之寺,原来如此的,清初的诗家文人常到的地方呵。”他自慰道。走到碧桃树下,忽然听见庙门外有汽车停留声,他的心又猛然跳起来:“她坐汽车来吗?”他脑中立刻现出一个富家女子,穿一身花绸衣裙,丝袜子,花缎子鞋或胶皮鞋,脸上涂了脂粉。
“这是一个女子的脚步声。走到后殿来了。迎出去?”他想着不知不觉便往前走了几步,不多会儿后殿山墙边转出一个女子来。他仔细一认,呆了一会才说出话来:“你怎会也到这地方来!”
燕倩笑着望他答道:“你怎会到这地方来?”幽泉愣着不知答什么。正想说话,燕倩已抢先笑说道:“告诉你吧!我听了一早上不爱听的话,心里烦闷的很,也想飞到郊外去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魂灵的——”
这时幽泉忽的脸上热起来,忸怩的笑着,向前一把抓住燕倩的手,高声说,“我又上了你的当了,哦,原来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播弄的花样。好好,你累我在这破庙蹲了一早上,我这回可不能饶你了。”
“得了吧,你那里料得到呢?”她笑着,同他向外走。“你该饿了。我带了吃食在车上,我们去找一个干净地方野餐吧。”他还搭讪着闹说不依她;她上车后取笑他“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嚷道:“还拿我开玩笑?如果不因为你车上已经带了吃的,我一定不依你。谁叫你写那封信,那样会说?”
“算了吧,别‘不依’我了。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
幽泉笑了笑答:“我就不明白你们女人总信不过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试探他。”
“幽泉你不要冤枉人吧,这那是试探?我今天打发你出来纯粹因为让你换换新空气,不用见不愿见的人,听不爱听的话罢了。难道我就不配做那个出来赞美大自然和赞美给我美丽灵魂的人吗?”
(初载1925年11月7日《现代评论》2卷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