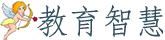太太在床上醒转来,想着昨晚的清一色和不成,正在生气那拦和的张太太,她的女儿放午学来家见母亲,第一句话就是要钱。太太睁眼骂道:“大早起来就要钱,怪不得打牌总输。怎么今天坐起车来?”
“我的脚冻了,走不动了。”大小姐呆呆的望住母亲说。蔡妈在旁向太太说:“本来已经十一月,该穿棉鞋了,学堂的姑娘们早就穿上。太太,您也该同大小姐买鞋了,这样皮鞋那是现在穿的。”
“什么东西都说买,有钱也不是这样花!上回我叫你买的鞋底子,不是预备跟他们做棉鞋的吗?”
“我不是提了您好几遍买鞋面,那知您一出门就忘了,没鞋面怎么做鞋?”蔡妈冷笑的答。太太觉得不耐烦,拿起床头的钱口袋往女儿身上一掷,愤愤的说:“费话少说,几个铜子数去给拉车的,歇会儿他又要麻烦了。”
大小姐正在发愣,没用手去接,不想这钱口袋重重的正掷到她长冻疮的脚上,痛得哇的一声低头摸着脚哭泣起来。但是她母亲盛怒之下,还未想到碰着她冻疮的疼痛,她想她不过为受了申斥撒娇便了。她一边下床,一边生气的说:“蔡妈去给车钱吧。这样大姑娘还不懂替母亲省省钱,才骂了一半句便哭起来。还有一个月就十三岁,过一两年就可以找婆家哪,还这样娇气。” 她回头看看女儿哭得更凶,索性坐在床前大椅上呜呜咽咽的把一件紫花布棉袄的袖子都擦湿了。
“哭吧,有本事哭一天!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像你姑妈,会向女儿赔错。”
她悻悻的出了卧房走到厅堂上。“谁出来进去总不关紧门,怕压了尾巴吗?”她坐在一张椅上觉得腰骨酸软,眼有些昏乏。
蔡妈拿洗面手巾胰子等来,笑说:“这是我方才端洗脸盆没有手关门了。” “老爷吃什么点心走的?”太太在洗脸问。“吃前天买的茶鸡子儿。”
“你怎的又拿那茶鸡子儿给他吃,他昨天不说那不是新鲜的,吃了它有点肚子痛吗?他回来,又该埋怨我了。” “他又不吃烧饼麻花的,不吃茶鸡子儿,那里还有东西了?” “不说你们不肯替我分分心,想想做些东西给他吃。那里会没有东西?炖碗鸡子儿也行呵!厨房里连鸡子儿都没有了吗?你们整天眼里心里就看见钱:人家买多点东西我们就闹底子钱,打回牌就要分头钱,来个客或送些东西就想赏钱。我真没法对付你们。那天不七事八事的支零钱,可是永远不会想想法替主人省些钱的。”她一边数落,蔡妈坦然的站在旁边伺候 她,觉得她主妇说的你们,并不是她一人,所以不觉到什么不舒服。她反笑说道:“太太,你想想那个人不为的是没钱,才出来伺候人!”
张升进来擦桌子,蔡妈望着他说: “张爷,方才你说那里打了两遍电话来给太太?”
“对了,方才有电话来,”张升说。“黄太太方才打了两回电话来,请太太今天早些去,她们都在那里等呢。”
“她还不说请太太带钱去捞本吗?”蔡妈作出很看不起人的样子笑着。 太太默默半晌,看见蔡妈的样子,想到黄太太藐看她没钱的“捞本”话,心下又气又恨,末了悻悻的说: “那一回我不带钱去打牌?输五十块便叫人去捞本,真看不起人,哼,告诉她,我五十块还输得起,今晚一定带去给她就是啦。” 蔡妈收拾手巾脸盆走,一边说: “她还嘱咐了几次叫太太务必带钱去。这次黄太太真瞧不起人,她还是您的亲戚,难为她好意思追得这样紧!我看太太这回争一口气索性把上回的 一齐还了她,省得听她那样饥荒话。连我听着都有气。”
太太一边喝浓茶,一边皱眉打算,好一会子才叫过蔡妈吩咐道: “把老爷的狐皮袍子和我的灰鼠脊皮袍子找出来,拿去远一点的当铺当九十块钱,别叫人看见你。” 蔡妈答应去了。一会取了皮衣服来,她说: “太太,您这衣服统统值多少钱呀,我瞧当不了九十块吧?”
“这狐皮的,买也值七八十块,灰鼠的旧了也许值五六十块的。” “这不行,当铺的规矩是凡值六七十的只可当二十来块,这两件至多只不过当出四十来块,便了不得了。唔,还许不行呢!上次那件耗子绒大褂比这个新,给人人看过都说值一百多块,当起来,那知道就值三十块。” 太太想了回子,又吩咐道:“把老太爷给老爷那件火爪马褂拿去吧!”
“那至多不过值二十块,也不够呀。我看还得加上一样东西。” 她站起进屋内寻了一会,又拿了一样东西说: “蔡妈把这金表也拿去吧。这个买时至少也用一百多块呢。现在加上总够了吧?”
蔡妈把东西包起,说: “我看爽性统统当一百块吧。” 太太见蔡妈要走不走,她低声道:“你不要给人知道。我看你的棉袄太薄,给你两块钱做一件吧。”
“谢谢您哪。张升就在套间,给他钱买鞋好吗?给他两块钱吧?”蔡妈又走近太太身前小声说:“他常常在书房同老爷谈话的。”
太太心下很不舒服,但她不愿示弱下人,说:“谈话会怎的?他要买鞋就给他两块钱就是了。” 蔡妈走后的半点钟,老爷也回来了。他今早上勉强吃了一个茶鸡子,觉得肚子又有些不好过,心下烦闷得很。回家来见女儿红肿着眼噘着嘴坐在一 边发愣,太太站在厨房门口骂厨子赚钱,他觉得一股乌郁晦气充满了家庭,也闷闷的坐在饭厅内等吃饭。
“为什么今天散班下得这样晚?”太太走进饭厅照例的招呼一句。 “早就散班了。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商议今天午后,一同去新任局长那里道喜——今天是他的老太太七十整生日。” “送了礼了吗?”太太坐下有些心烦的问。 “我们是合份的,一人十五块呢,也没法不应酬!趁着没开饭,你叫人把我的狐皮袍子火爪马褂拿出来,吃过饭就得走。”
太太浑身不舒服,过了一晌,她勉强装作镇静的样子,答道:“你……你的狐皮袍子和马褂不是那天借了给姑少爷了吗?” “那天?赶紧打发人取出来吧。” “他现在不会在家吧?”太太很不自然的说。 “方才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没穿我的衣服。赶紧打发人去取吧。”他看住她答。 “哦,我记错了。没借给姑少爷,大概是张六爷那天来穿走了吧。” “张六爷去天津了。他也穿不了我的皮袍。你到底借给谁,快仔细想想,叫蔡妈他们来问一问。眼看快两点就得走的,你看我今天这件袍子那能去拜寿?我的身格又特别小,借也借不到合式的,况且我的朋友里,谁也没有多余的体面衣服借给人呵。”
太太望了望老爷假毕几呢面的羊皮袍,袖子已有些露出皮子,大襟脏了 一大片,不知答什么。她想哭也哭不出来,只说:“你今天推说有病不去行吗?那件袍子马褂我真记不得借给谁了。” “前几天就有人通知我说,新局长要好好的换几个人,叫我务必不要给他找着岔儿。我又没有大来头撑腰子的,那能不去?今天我怎样也得去 的,你到底借给谁了?快打发人去取吧。”
太太默默的望着墙,眼内含着泪。老爷望着墙上挂钟,还连着催问她。见她不答,他急得站起来走向她身前逼问: “时候不早了,到底的借给谁,说出来好取去呵。今天我不去就把饭碗弄掉!”
她看丈夫急得眼发直,声音抖擞的可怜样子,末了的话尤触动她的心,后悔方才自己不该太大意。她被丈夫逼得太紧,反而一句话讲不出,直流眼泪。
她丈夫见她流泪不语,更加着急,说:“我的衣服放在家里的,谁拿去,你总该知道。我只管向你要:说话呀,这不是哭的时候。”
此时饭已端上来,他气愤愤的坐近饭桌,催她:“到底放在那里?你也得替我想想,我不去是不行的。这份差事没了, 咱们上那儿找饭吃?”
太太听了这话,更加着急,她抽咽的向张升说:“你赶紧到街上追蔡妈回来吧。”
“怎回事,给蔡妈拿去啦?”老爷急回头望她。“她去了已经有半点多钟了,谁知她现在在那里?”张升答。 “到铺里找她。”太太急答。 “她只说您叫她上远一点的当铺,谁知她去那一间?”张升答完,站在一旁。 老爷听见当铺二字,忽然大悟皮袍的着落。
“哦,原来当了,怪不得你不出声?你当这些钱做什么?”他见她只哭泣不答,把饭碗放下,紧望着她问:“当在那间铺子,还不赶紧打发人去赎回来?”
太太只得收泪断断续续的吩咐:“张升,你……快……去找蔡妈,叫她快……快回来!” 张升噘着嘴走出去。
此时老爷觉得衣服有了下落,拿起筷子吃饭。但那菜同饭都凉了,天气又冷,他心火又盛,所以觉得十分难吃,吃了一口快要冷的菜汤,肚子又隐隐作痛。他想到今早上的冻茶鸡子儿便望着太太数落起来:
“三十多岁的女人还不知道顾顾家,整天在外头打牌……” 大女儿已经出来等吃饭,她站在火炉旁边,痴望着父母吵架。母亲没上饭桌,她也不敢去。老爷愈吃愈觉得无味,把筷子一摔,向女儿道:
“大妹吃饭罢,别等你娘了。哼,这样人还做母亲哪!” 太太此时正要收泪,忽听见老爷末了一句话,不觉大怒,她跳起来说: “我怎样不配做母亲?我倒要你说说。你说别的我不管,你当着我的女儿,这样糟踏我,我不答应!”她说着走近他身前瞪直了眼。 老爷正拿住碗喝茶,看她猖狂情状,气得手抖。只听乒乓一声,一碗热茶正洒在太太手上,烫得她呀哟一声,喊着哭起来: “要烫死人啦!要烫死……”她索性往老爷身上碰。 老爷赶紧跑出饭厅,使劲将屋门一摔,算是报复,连忙戴上帽子上朋友家去了。
太太索性坐在地上哭起来。屋内只有她女儿,她也不懂怎回事,也不知道搀她娘起来,也不知道劝解。她站在炉边,不想火旺起来烤得冻疮渐渐好似针戳一样,阵阵痛痒。肚子又饿,头就昏晕,十分难过,末了也呜呜的哭起来。
邻居老太太听见哭声,赶紧过来劝解。太太照例数落了一顿老爷没良心。
老太太也帮助着好歹的埋怨几句。到了三点钟,太太已经洗过脸吃过炒饭。 老太太大功告成的走回家,蔡妈也回来了。
“太太睡着了吗?”蔡妈见太太正掩衾假寐。“哦——今天好容易同铺里人说了又说,才当出一百块,他们起先拼命说东西只值八十块呢。” 她把当票同钱交给太太,并说: “这是九十五块零两吊。太太给老张两块,我两块,我又化了些车钱,在那里等了半天饿得肚子痛,又要了些东西吃。”
太太懒懒的把钱接过来说: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方才急死人哪!想找你也找不着。”
“厨子把方才的事告诉我啦,那家子俩口儿一个月不吵几回嘴?太太也犯不着那样难过。”蔡妈轻轻一解说,太太也觉得方才大哭是过分了。
一会儿厨子来报说黄太太来电话催请,牌手都坐齐了等。 太太从床上起来拢了拢头发,换了身上衣服,雇了部洋车就要走。 “我不去,好象要赖她们的帐。”她走近门口停步又说:“回头老爷回来,别提我去那里呵。” “太太,”她方出大门口,蔡妈叫住说,“您还不如放下钱,等我去同少爷买操衣布吧。省得他回来又哭了。他今早哭吵着不肯上学堂去,说先生前天已经告诉他,再不穿操衣,不止罚站,还不许上学呢。我们好容易哄他去, 说今天包管给他做好。还有小姐的棉鞋面子也要快些买了。”
“讨厌,早不要钱,晚不要钱,偏偏我出去打牌才要!今天先别买吧。” 太太灰着脸,吐一口吐沫,坐上洋车去了。
一九二五年末一天
(初载 1925 年 12 月 1 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