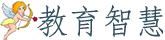一个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
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光脚拖木拖板,爱玩爱笑爱打扮。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困苦,成千成万的女孩子,还没有长成少女,就要去谋生。又没有正经的生路,只好去当“下女”,去做“女招待”……每当夜深人静,我听着窗外马路上,格拉格拉的木拖板声音,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爽朗的成串的笑声,我就寻思台湾姑娘的性格,可总是抓不住要点。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眼见她一二年间,忽然长大成熟,又忽然枯萎谢去,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为了生活,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远离城市,宿舍又远离学校。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经过了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弄得围墙倒塌,门窗破败。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了。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又听不懂本地话,没有一个朋友,活像被充军到沙漠上去了。
有一天我上课回来,推开房门,不觉呀的一声,仿佛走错了人家。那挂在墙上的脏衣服不见了,摊在“塌塌米”上的被褥叠起来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最难得的是一股清凉的气味,那是“塌塌米”刚用凉水擦过了。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从破败的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低着头刷洗锅碗。只能够看见半边脸,脸色又白又干,仿佛石灰。她像是怯生生地看我一眼,没有抬头,也不说话。这就是好心的台湾同事,给我找的“下女”。可是这么小,行吗?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娃莫栽。”
“家住哪里呀?”
“娃莫栽。”
“不要害怕,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
“娃莫栽。”
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知道“娃莫栽”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想必我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吧。我回到房里,拿一张纸,写上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再拿出十块钱,一起交到她手里。还没有解释什么,她就静静地一笑,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
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全部搬出来,再捎带上几个日文单字,外加指手划脚,向她说明早饭午饭的时间。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穿衣服向来不讲究,用不着天天洗换。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可是必要回答的时候,总是一声“娃莫栽”,或者静静一笑。我疑心这笑里面多少有些狡猾。并且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啊,不是一个小姑娘,人家很有心眼儿哩。
从此,这个破败的日本式小房子上有了炊烟。荒凉的院子里挂起绳子,晾上衣服。白天有人把窗子打开,让阳光进来。有天晚上,我坐下来写字,叫她沏一壶茶。往后天天晚上一坐下来,就听见她从厨房里,格拉格拉走过来。到了房门口,甩去木拖板,赤脚走上“塌塌米”,双膝跪下,把茶盘放到矮桌子上。这跪下原是日本式的日常动作,既有“塌塌米”,又是矮桌子,好像也只有跪下比较合适。可是我总不习惯,觉得自己享受过分了。每天她放下茶盘之后,就把捏在手心里的一片极小的小纸头,往桌上随便一扔,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纸头上写的是柴米油盐几个大字,每个大字下面注着钱数。我费了许多口舌,说明用不着这种日报制度。她只是回答一声:“娃莫栽。”有一回我假装烦恼,当面把纸头撕碎,这才不再拿来了。可是我发现厨房墙上挂起一个小本子,那是日记账。啊,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
我是一个流浪的光棍汉,人地两疏,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心里充满了感谢。可是一天又一天,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娃莫栽”。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她仔细地固执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一概不信任。有回我苦脸告诉她,不知叫她什么,只好叫做“娃莫栽”吧。她先是静静一笑,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笑得直不起腰,两手捂脸,跌坐在台阶上。可是忽然打住了,笑容不见了。好像风筝断线,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这一刹那间,她明明显出心事重重。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的心事,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
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只打听到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高小毕业生。家口重,就念不起书了。我想一个教书的人,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真是叫人难过。我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教她国文。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有天我到厨房里去,看见她捧着本大书。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我抢过来一看,却是日文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吃了一惊,说了一句愚蠢的话:
“看得懂吗?”
“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叫道:
“你很用功,好,很好。要学国文吗?我教你,我有时间,学吧,你学吧。”
“娃莫栽。”
此后每天晚上,我们上一小时的课。上课当中,我才知道一般的国语,她全听得懂。国文程度,也够高小毕业的了。
过了三个月,我第一次让她作文,不出题目,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她写道:
“我要努力学习国文,赶快学好。明年我要考中学去。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有了饭吃。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也有了饭吃。他们有饭吃,还使得我亲爱的母亲用不着吃饭了。
从此我笑不畅快,玩不起劲。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这样很好,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上学本是我的梦想,可是料不到,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实现的。因此,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我要赶快学好国文。”
我常年看作文卷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的动心。老实说,流下了眼泪。并且立刻背下来了。我是小心谨慎的人,平时牢牢记着,哪些话不能出口。可是给她上课时,我竟和她一起读报纸。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在字里行间,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势。
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聪明伶俐的女同学。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许多接近的机会。可是我胆小,生怕句把难听的话,几下不得体的举动,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离开中学以后,我过着贫穷的流浪生活。寒酸潦倒,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了。现在我竟得到这么舒坦的日子,天晓得她怎么摸透我的一些穷讲究:我不爱书桌上插花,花瓶得搁在窗户台上。衣服不摆在眼面前,是想不起换洗的。又怎么知道凉水擦过“塌塌米”之后,那一种清凉的气味,能叫我心醉。这些琐碎事情,我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
到了年关,正月初一的早上。她从家里赶来,穿了一条新做的墨绿裙子,上身是青缎外套。从青缎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本是母亲的衣服。她静静一笑,鞠了个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恭喜新年。”
立刻钻到厨房里去了。我赶紧叫道:
“不吃饭。早就说过的,初一到初三,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要出去玩一天。对了,进城玩玩去。对了,你也去吧。
对了,去吧,一起去吧。”
在姑娘们面前,我永远只会慌里慌张地,装做偶然想起,才能提出要求。可是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一点反应也没有。管自格拉格拉走来走去,收拾屋子。我只好拿起报纸,闷闷看着。好一忽儿,听不见格拉格拉的声音了,抬头一看,见她笔直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田野。我忽然想道:难道是等我出去吗?赶快走到她身边,说:
“多好的天气啊。”
她就静静地跟着我走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一些同事,还有邻近学校的教职员们。
不论是谁,她都点一个头,用国语或台湾话,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我奇怪她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不想她回道:
“认不认得,过年总要问好的。这是礼节。”
惭愧,我竟不懂得这么好的礼节。可是我觉得那些认得或不认得的人们,都用一种尖利的眼光看着我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惭愧,她好像不在意,照样静静地,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进了城,我慌忙带她走进一家清净的咖啡店。对面坐下之后,我发觉她的眼神里,透着猜疑,忧虑。可是她一字不提,全部埋在心里。可是又全部,叫黑白分明的眼睛泄露出来了。
我猜度着说道:
“别管人家,我们玩我们的。”
“什么?”她好像不懂,但又立刻明白了似的。说:“没管人家呀,管那些做什么呢?”
“看你好像有些不安心。”
“过年总要算算账的。昨天晚上我爸爸对着账簿,坐到下半夜,抽完一盒烟,说,我们家很穷啊。你大哥二哥都为着真理,给抓走了。我这个老牛,还可以拉几年车子。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你们也要有一个为着家,为着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简简单单地说:“爸爸要我什么也别管,一心学医去。”
“学医也很好啊。”
“啊。”她闭上了眼睛。当睁开来时,神色很安静。说:
“老师,你留心没有?听说有时候校长偷听你讲课。”
我心里一跳,怎么她也知道了呢?我秉性谨慎,但又绝不说谎。到了真话不能明说的时候,就不作声。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新文学史,都是只讲到“五四”,就声明讲不下去了。
可是作家总是要讲的,我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几次发觉,校长悄悄闪在窗外,壁虎那样贴着墙壁站着,听我讲课。
生活经验告诉我,早晚要卷铺盖走路了。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见什么风声了?”
她摇摇头,却说:
“也有的老师,课堂上不讲什么。课外找一些好学生,搞读书小组,读课外书。”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声音轻悄悄的,样子多像个文静的女学生。可是说的话又很沉重。我竟不明白这是她自己的话,或是别人让她告诉我的。因为这一番谈话,我觉得我们互相间又多有了一些了解。我觉得她的内心比她的年岁要年长得多。但这一天玩得总不爽快,仿佛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来到了。
正月初五,学校里摆酒席聚餐。那校长原是个小官僚,酒量可以跟酒缸比较的角色。从黄昏一直喝到十点钟,越喝说话越多。教员们轮流站起来向校长敬酒。最后有个教员竟把校长扶上凳子,有人叫好,有人跑过去帮忙,竟从凳子上又扶到桌子上面。叫我们大家围着桌子,举着杯子,为校长干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放下杯子,从人堆里挤出来,走出屋子。我听见乱哄哄的声音中,校长冷冷地说道:
“共产党。”
我考虑了一夜,觉得俗话说得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清早起来就收拾行李,“娃莫栽”好像不觉得意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帮我捆捆绑绑的。当我雇好脚夫,回头却看不见她了。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我心慌了,走到厨房窗口,只见她笔直站在窗里,脸色石灰一样又干又白,脸上挂着两行眼泪。她一动也不动,只是手指头哆嗦着。手里抓着一张我的名片,那原是贴在房门上的,不知什么时候她拿下来了。看见这种情景,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盘乱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反倒拔脚跑出院子。冬天的早晨,铁青的天色,荒凉的田野,哭泣的风,一挑行李,我踉踉跄跄上了路,走出里把地,终究忍不住了,猛的回头,从倒塌的围墙缺口,看见了破败的厨房小窗。窗里黑糊糊的,可是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娃莫栽”当窗站着。手里拿着我的名片,脸上挂着眼泪。我很难过,仿佛是一个丢下亲人,管自落荒而走的家伙。
进了城,我找一个朋友借路费。那朋友在职业学校教书。
职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员,就把我留下了。要我教国文之外,兼教两班地理。地理上头,我完全外行。可是朋友说,走上讲堂,拿起粉笔,随手画出一个省的轮廓。再添上主要河流,几条山脉,有这一手,就是地理教员。一个学期不过教三四个省,离开学还有半个月,还怕练不会这一手吗?我想想无路可走,只好去练画地图。我生怕日后闹笑话,就命令自己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画呀画的。
开学的那一天,我参加了开学礼回来。正打算坐下来准备三天之后的第一课。猛的听见格拉格拉的声音,直走到门口,甩去木拖板。听得这样真切,我的手都哆嗦了。我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外面,我背上发毛。猛的回头一看,啊,当真是“娃莫栽”。她静静笑着,见我回头,就双手放在膝盖前面,深深行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老师好。”
来得这样突然,我慌里慌张地招呼她坐,喝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小包,随便往屋里一撂,就去看满墙的地图。一下子她又钻到厨房里去了,我听见打开水龙头又关上,揭开锅盖又合上。她从厨房里出来时,皱着眉头,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我赶紧说:
“不用忙,别着急。你看,叫我弄得乱七八糟。你休息休息再整理吧。”
她稍微一愣,随即静静地笑道:
“爸爸不让我当‘下女’了呢。”
“那好,那好。”
“我考职业学校好不好?”
“好啊,好啊。”
“今天来考,不就晚了吗?”
“是啊,晚了。”
“不晚,不晚,我早考了呀。”
“啊,啊,好啊,好啊。”我连声叫好。一边又因为自己总把人家当做“下女”,脸也飞红了。可她已经拖上木拖板,走出大门。我叫道:
“慢着慢着,考上没有?”
“娃莫栽。”她管自走了。
我回头看见撂在屋里的小包,叫道:
“慢着慢着,忘下东西了。”
“娃莫栽。”
我打开小包一看,却是一盒糕点。明明是一件礼物。我忽然想起她的对着账簿坐到半夜的老父亲,我的眼眶湿了。
以后有两天没有看见“娃莫栽”。我第一课教的是江西省,我把江西的轮廓画了几十遍,越画越像一个少女的头部剪影。
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第三天早上我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好像一个市集。我走进教员休息室,看见同事们都一声不响地呆坐着。我的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昨天下午,台北爆发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人民反抗蒋政府的统治,包围了行政公署。罢工、罢市、罢课,今天连火车都不通了,恐怕全省都要响应了。——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起义。
上班钟响了,没有一个学生往教室里走,却在操场上排成队伍。一个大个子的学生上台喊口令,一个女学生向大家交代什么事情。不料这就是“娃莫栽”……我着了魔似的,从玻璃窗里看着学生们唱起进行曲,喊着口号,打上旗帜,齐步走出学校。刹那间,我的中学时代涌到眼前:高喊着抗日救亡,罢课,游行……当年的生活多么爽朗,生龙活虎。现在我却这样孤独,软弱,好像一条灰不溜秋的耗子。我的心头擂鼓一般跳动,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接到校方的通知,说是言语不通,可能引起误会,不要离开学校一步。我推磨似的在屋里团团转了一天。晚上,七八个学生推开我的房门,问我有手枪没有?有子弹没有?有别的武器没有?“娃莫栽”跟在大家的后面,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我们从不相识。有一个学生解释说,恐怕引起误会,武器还是交给他们保管的好。我看得出来,这是变着法子搜集军火。听说话,他们仿佛把我归到敌人那一边去了。我无话可说。“娃莫栽”第一个走出屋子,学生们都跟着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好像钉子钉到我脑子里去了。他们要手枪干什么呢?难道这是用枪的时候吗?嗐,没有一点学生运动的经验!不知道三五支枪,反倒会坏事的呀!“娃莫栽”,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跌跌撞撞摸到学校里,看见有个教室灯明火亮。我闯了进去,没错,这种景象我熟识得很。课桌都已拼凑到一起,铺开纸笔,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画漫画。我故意不看“娃莫栽”,不看任何人,不管四面八方尖刀似的疑问的眼光。
我大声说明自己也当过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我有一点点经验,愿意贡献我的力量。说话之间,我的眼角觉察到“娃莫栽”跟几个学生咬耳朵。等我说完话,立刻受到学生们爽朗的欢迎。不知怎么的,“娃莫栽”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把我按到椅子上。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笑着,笑着。就是这种场合,她的笑也带着静静的味道。
当晚,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代表。一组到台北联系,一组去台中。“娃莫栽”是到台中去的一个。天蒙蒙亮时,他们上汽车走了。
我的青春回来了。虽说经过了特别寒冷的冬天,可是当大地醒过来时,冬天的冰雪也变成了泥土的营养了呀。我自信比学生们还要壮健。可惜,可惜我们还没有站定脚步,街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兵们随时随地可以实弹射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娃莫栽”还没有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校里禁止我外出,就是不禁止我也无路可走。我把牙膏牙刷,换洗衣服,收拾在一个小提包里,准备随时被捕。有回我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叫喊,虽说焦急万分,可还是咬字分明:
“……青年们,工人们,赶快到台中车站去,我们的人被包围了。学生会,学生会,赶快带领队伍,用一切交通工具,支援台中车站……”
卡擦一声,收音机不响了。无论怎么扭怎么摇,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当天下午,有两个打手请我到校长室谈话,其实却把我架上了汽车。当晚,我被抛进了一个秘密监狱。
这个监狱本来是几个连串的钢骨水泥的大厅。现在厅子和厅子之间,安上铁栅栏。每个大厅里,安上三排木头笼子。
每个笼子都是两面板壁,两面碗口粗的木头栅栏。人关在里面,活像动物关在动物园里。
有天早上,我和一个难友抬着尿桶上厕所去。经过中央的小厅,那是特务们办事的地方。那厅里有一面穿衣镜,只要门开着,我总要顺便照一照的。那天我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女孩子,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脚下撂着一个小包。这女孩子不慌不忙地梳着,好像在自己家里。这女孩子忽然往边上挪动一步。啊,镜子里照出了我,还有一个“娃莫栽”。她在镜子里静静一笑。厅里有个人咕噜一声,我抬着尿桶走了,但听见“娃莫栽”提高嗓子和人说话:
“是啊,我一点事情也没有,也送到这里来了。”
镜子里的形象,叫我久久不能忘记。我头发蓬松,脸色青白,潦倒得不像人样。可是我旁边梳着头发的“娃莫栽”,她那样安静,笑得那么平常。
常常三更半夜,特务们在小厅里审问新来的难友。夜深人静,我们可以听见一些声音。我等候他们审问“娃莫栽”,夜夜提心吊胆。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有天我头昏脑胀,矇眬睡去。梦见她就在我的面前,上下左右不知多少根皮鞭子,毒蛇一般缠咬她。可是她静静对着我笑。我心里针扎一般猛的惊醒,我听见远处有人喝道:
“还笑?还笑?”
那人念咒似的呜噜呜噜了一阵,我听见一声熟悉的回答:
“娃莫栽。”
我飞快爬到栅栏旁边,耳朵塞在栅栏空子里。我听见拍桌子,跺脚,骂娘。还是一声平静的回答:
“娃莫栽。”
我听见有人狼一样大嗥一声,我从地上猛的跳起,可是听见那句平静的“娃莫栽”,我又爬下了。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音,铁器碰撞的声音,木头敲打的声音,我跳起爬下,爬下跳起,咬牙咬得牙关酥了,攥拳头攥得手抽筋了。我的心那样翻腾,仿佛一下子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了。每当我忍受不了的时候,都听见那一声平静的“娃莫栽”。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忽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浑身的冷汗,可是抬不起手来擦一擦,立刻昏过去似的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又忽然针扎一般惊醒,夜正深沉,可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暗暗发誓,跟这些野兽战斗到底。我觉得从这一夜起,我才去清算贪生怕死的念头。从这时开始,才变成一个有决心的人。
此后没有“娃莫栽”的消息。一天中午,一个小看守大步走到我的笼子外面,咣唧打开牢门,恶狠狠地喝道:
“出来!”
我毫不害怕,也狠狠瞪了那看守一眼,走出笼子。他带我走到通往另一个大厅的铁栅栏旁边,趁打开铁栅栏的工夫,低声说道:
“顶多三分钟,左手第二间。”
我赶紧跑过去,“娃莫栽”靠着木头栅栏坐着。脸是这样白,下巴颏这样尖,眼睛这样亮。我仿佛第一次从厨房窗口看见她,心想多小的小姑娘啊。我心里一酸,眼泪出来了。可是她对着我静静一笑,我勉强忍住眼泪,并且有些害臊。她问我吃得下不?饱不饱?三分钟就过去了。当小看守过来催我走时,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叫道:
“啊呀,脏死了,脱下来脱下来。啊呀,鞋也破了,脱下来脱下来。”
我来不及考虑,脱得赤膊光脚跑回笼子。第二天,我收到干净衬衫,鞋子也缝上口子了。真像是奇迹。
这是一个秘密监狱。可我们要是出得起够多的价钱,也能够让小看守从犯人的家属那里拿进来一些东西,也做得到把必需品送给难友。这种互相赠送日渐增多,不知什么道理,“娃莫栽”常常能够走到铁栅栏旁边去,她那里成了两个大厅的交换站。这种活动,解决了一些难友的物质困难。重要的是,给了人体贴的鼓舞,日常的亲切的快乐。而更重要的是,借着衣物来去,交换了消息,传递了字条。我也利用各种机会,走近铁栅栏,跟“娃莫栽”说上几句话。当我积极参加这种活动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在做好事,内里是有组织的。当然活动只能在个别小看守当班时进行,绝不能够叫看守长知道。有天早上,我们排着队抬尿桶上厕所去时,“娃莫栽”塞过来一条内裤,一个新来的难友接过去了。“娃莫栽”嘱咐道:
“传过去,传给十八号。”
可是那位难友却揣到自己的怀里去了。“娃莫栽”看见我在十步开外,大声叫道:
“快来快来,裤子裤子,给十八号的。”
当我放下尿桶,超过队伍往前去时,听见一声断喝:
“嚷什么?谁叫你上那儿去?上那儿去干什么?”
原来看守长来了,他好像立刻要吃人似的瞪着“娃莫栽”,我站住了脚。大约“娃莫栽”以为我没有听明白,用眼角望了看守长一眼,不慌不忙地盯着我说:
“你们看见一条裤子没有?刚才撂在这儿的。穿都穿不得了,可是裤腰还是好的,我舍不得丢了。”
我马上想到裤腰里塞着什么字条吧。
那看守长大吼一声,伸手一推,我就看不见“娃莫栽”了。
当我从厕所回来时,听说“娃莫栽”已被押到黑牢里去了。黑牢在地下室里,不知那里是什么景象。传说关上三个月,人会神经错乱的。我们等候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还不见“娃莫栽”回来。起初还天天打听,后来提也不敢提起了,为的怕说穿那悲惨的结局。我常常在夜里,心口无数针扎一般惊醒。轻轻叫着她的名字,眼睁睁到天明。有天夜里,我听见墙外飞过一只布谷鸟,叫了一声布谷。好容易忍耐到天亮,我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到别的笼子里去。可是从别的笼子里,却传来一个压倒一切的消息:“娃莫栽”回来了,并且就在我们这个大厅里,在第三排转角的那一个笼子里。
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海边涨潮一般,涌上来无数的浪头,心里边涌现许多计划,怎样走到第三排转角那里,看上一眼,说两句话。我们住在一个厅子里,可是任凭我千方百计,总共只见到她四次。
第一次——
我三脚两步往那里去时,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木头栅栏,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轻脚轻手走到她面前。她的脸色石灰那样干燥苍白,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又闭上了。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一点也不稀奇。我禁不住吃惊,“啊”了一声。她又睁开眼睛,她的脸上这才闪电一般出现了兴奋的表情:
“你来了,来了,看见你了,不是做梦,真的看见了。”
“刚才你好像没有认出我来。”
“不是,不是,我当是做梦,我常常做梦,闭上眼睛就是梦。”
她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断成两三句。她的嗓子沙哑,必须用力说出来,才有常人的声量。我心里一哆嗦:
“黑牢里很苦吧?”
“不,不,没有什么,不要紧的。”静静一笑。“我不是好好的吗?”这句话没有用力,就沙沙地,勉强才听得清楚。
“听说那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不,不,那里晚上亮一点,晚上比白天亮。走廊里有些路灯,漏进来一条光,总有手掌宽。晚上我是不睡觉的,我看书。凑着那一条光,把‘唐诗三百首’里,读得懂的都背下来了。”
“唐诗?”
“有天夜里,我听见地板上有个东西在抓在爬,啊呀,好像大得不得了,总有一头熊那么大吧。那东西爬到光里面来了,原来并不大,是个小耗子,滚圆精壮。它见了光,眯起眼睛,两支爪子扒拉扒拉胡子,有趣极了。我笑了出来,可它一点也不害怕。想是先先后后的难友们,把它喂惯了吧。它跟我捉迷藏似的,一忽儿出来了,一忽儿不知哪儿去了。我满地里找耗子洞,却找到一块活动的地板,弄开来一看,有一本唐诗……”
她累了,静静一笑,闭上眼睛。
“你躺躺吧。”
“不,不,不。”
“白天呢,尽睡觉吗?”
“尽做梦。睡一忽儿,梦一忽儿,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梦着呢,还是醒着呢。”
“都做些什么梦?”
她静静笑了一忽儿,眼睛里闪着快乐的火花: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家里。我用凉水擦过了‘塌塌米’,屋里清凉清凉的。我站在窗边,等我哥哥回来。啊呀,院子里围墙早已修好了,爬了一墙的牵牛,一墙的紫的玫瑰的白的蓝的小喇叭。香蕉树有房子高了,椰子树碰着云了。地上满是五色草,紫的白的绿的墨绿的。土名字叫没根活。掐下一节往哪里一插,它就能活。真是好东西。我抬头一看,怎么你来了……”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怎么这样说呢?不,不,这样说也没有什么……”
她一低头,头顶顶着木头栅栏。不知道是她累了还是我说话莽撞了。我说:
“对不起,我说了没有意思的话。”
“不,不,不要紧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在家的时候,也种花草,可也不见得特别喜欢。偏偏来到这种地方,常梦见花园,看见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花朵……”她静静一笑:“是不是那时候我还小,现在我长大了。”
“一共也没有多少日子吧。”
她笑笑,轻轻地沙沙地说:
“这些花朵叫人多喜欢哪。”
我听见几声咳嗽,由远而近。那是难友们传递过来的信号。有什么家伙来了吧。
“你走吧,走吧,慢着,老师,‘浑欲’是什么意思?”
“浑欲?”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哦,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是呀,是呀。”
“差不多,几乎,快要。”
………………
第二次——
我拿着一包烟卷大小的牛肉干,急急转过弯。“娃莫栽”盘腿坐在地上,脸儿嵌在木头栅栏中间,望着我的来路。没等我走到面前,就急急叫道:
“九天了,等了你九天。前回一句要紧的话都没有说,问你,一冬天你做了些什么?”
“做是做了些事情。”
“做的顶多的是什么呢?”
“瞎想。”
“想的顶多的是什么呢?”
“生和死。”
“啊!”她叫了一声,好像见到一样叫人受不了的脏东西。
“怎么了?不舒服吗?”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不画地图呢?”
“地图?”
“你是地理教员呀!”
“那是笑话。”
“不,不,你的地图画得不错。想办法画几张,画一张东北,画一张山东。画上战线,画上由哪里打到哪里了……”她张了张嘴,忽然说不出声音来了。我赶紧说:
“我画,画。你休息,休息。”
她喘了口气,静静一笑,用力提高嗓子,可是我只听见轻轻的沙沙的声音:
“不要紧的,刚才说急了一点。你读了些什么书?”
“哪有什么书读呢?”
“为什么不学日文?”
“怎么学呀?”
“你的环境这样好。”
“环境好?”
“是呀,你跟大家住在一起,大家差不多都会点日文。连看守骂人,都会用上几句日本话的。为什么不学呢?”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我听见日本话就心烦。”
“不,不,不对,那不对。你教我国文的时候,跟我说,学好一种语文,就好像灵魂上打开一面窗子。你看你的条件又这么好,……”
“什么条件?”
“有时间呀。”
“好,学吧。这是牛肉干,拿着。”
“不,不,我不要,我有吃的东西。我吃得很香,你拿回去吧,谁送我东西我都不要的。”
“你身体弱,你要保养。”
“不,不,大家都要保养。我也不弱。真的,我身上哪儿也没有毛病。我很快活,真的,做了那么多梦,没有一个不是快活的。”
“拿着吧,这点东西来得不易。”
“怎么来的?”
“一个难友的妹妹,花了不知多少钱,才送进来一点东西。
听说那妹妹在外面出卖肉体……”
“啊!”她干叫一声,闭上眼睛,低下头,顶着木头栅栏。
想不到这么句话,使她这样受不了。
“对不起,我说了句粗话。”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到了这里,什么粗话没听见过呢?可你,可你说的是难友的妹妹呀,……”
我听见值班小看守大吼一声,那也是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有人来了。
“去吧,回去吧。第二排有个病号,你带给他去。慢着,你别说怎么来的。你告诉了人家,叫人家怎么咽得下呢?”
…………
第三次——
我轻轻走到她的笼子前面,她闭着眼睛靠在栅栏上。她的头发齐齐盖住半边脸。这头发是一种奇迹,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整齐的。她这样安静,这样苍白,仿佛坐在窗口看月亮,看着看着睡着了。我一向觉得她长得美丽,可是说不出来美在哪里。仿佛只是五官匀称,此外没有什么特征。这一回我发现她脸上的线条特别细致特别明确。眼睛的弧线,鼻子的直线,嘴唇的弓形线,都是明确端正,又细致柔软的。我轻轻叫了一声,她立刻睁开眼睛,一下子睁得那么大,一下子就完全清醒了。我从侧面看出,啊,美丽的眼窝深深凹下去了,眼球又像是离开了眼皮,凹在尽里面。可又黑白分明,没有一根红丝,没有一点点肮脏。
“又梦见什么了吧?”
“你去过阿里山没有?你没见过那里的云海?没到过原始森林吧?我在山上住过一夜。那一夜光想一辈子在森林里工作。我们的森林工人里有各种各样的好人,有学校课本里所说的懂得鸟语的公冶长,瘦高条,山羊胡,戴高帽子,穿宽袖大袍。有‘猎人笔记’里面外号叫做跳蚤的小老头儿。森林里没有路,公冶长叽啾叽啾地问鸟儿们:‘哪儿去?往哪去?’鸟儿们叽啾叽啾地好像回道:‘往西,往西。’要知道树是不能乱砍的,有一定的尺寸。还要留下母树,让她撒种子。跳蚤小老头儿走路一跳一跳的,老是弯下腰,招下这个花那个草,揣在怀里。一路上嘟嘟囔囔跟树木商量,让谁留下谁又愿去。有天晚上,我们并排躺在帐篷里,呼噜呼噜,大家睡得好香好深沉。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迷迷糊糊的睡不踏实。半夜,我并不知道是在做梦,听见一声一声替拖替拖的声音,仿佛一个高大沉重的巨人,拖着拖鞋,一步步往我们这里来了。
一掀帐门,进来的却是个瘦骨伶仃的小老太婆。头发雪白,眼珠子绿幽幽的,手里拿着一根麦秆。她从门口起,挨着个儿,用麦秆往我们头上吹气。我睡在当中,眯着眼睛看她一个一个吹过来。到我这里时,赶紧闭上眼睛,忍住呼吸。只觉得她这口气冷森森跟冰水似的,把我浑身冻僵了。我这才想起她就是森林妖婆啊!我知道应该立刻爬起来,要是我一起来,大家就会一个跟着一个起来的。我们冲到帐篷外面,绕着帐篷跑三圈,就没有事了。要是起不来呢,大家全会冰凉僵硬了。可我怎么起得来呀,手脚全不听话,身体软得跟棉花团一样。我想叫,张了张嘴,一点声音也出不来。啊呀,森林妖婆已经吹到最后一个人了,再起不来就晚了,晚了。我急出一身大汗,还是动弹不得。忽然想起,咬一咬舌头试试。一咬舌头,我就刷地坐了起来,挨着我躺着的,也刷的跟着起来了。我想对了,行了。一骨碌就冲出帐篷,一个跟着一个,公冶长,跳蚤小老头,都冲出来了。他们都闭着眼睛,都还没醒呢。我领头绕帐篷跑了三圈,回头一看,森林妖婆也跟在后面跑。不对,不能站下来,我就再跑,再跑,跑得气也喘不上来了。可是森林妖婆还在跑呀,我想完了,再也跑不了了,腿抬不起来了,要晕倒了。可是我若跌倒,大家都会随着跌倒的。还得跑呀跑呀,哈,森林妖婆一个跟斗,栽在地上。我只多跑出一步,也摔倒了……”
…………
第四次——
“啊,你怎么来了呢?快走,快走,今早大检查。你们不知道吗?快通知大家。”
“知道,我们都知道。可是十二天没有看见你了,就是会把我弄到黑牢里去,也要看看你。这十二天里头,我想了上百个办法,都没有来得了。真他妈的……”
“啊!”她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我嘴上也学脏了。”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她静静一笑:“我看见你画的地图了。有一张还有两句日文说明,你学了日文了。”
“别提那个。我想了十二天,一定要告诉你,要跟你说,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有你在一起,我……”
“我不懂什么力量,别说了。不,不,今天你很高兴,一定带来了喜信。不,不,今天是大检查的日子呀,说了可惜了。”我看她说话比往日更加用力了,额上竟渗出一些汗珠。
可是声量比往日还要弱些。
“那我不说了。你躺着吧,我走了。”
她用力提高嗓子:
“慢着。你觉不觉得,我们好像住在一条轮船上?”
“哦?”
“这里是一间一间轮船上的房间。不过是在顶底下的一层,好像在货舱里。我从前坐过这样的货舱。这条轮船走得慢极了,死沉沉地。人呢,天天闷着。弄得好些人不知道往374小说B林斤澜:台湾姑娘哪儿去了,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拢岸。”
“我们要多做些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指南针。”
“对,指南针。”
“是啊,你多想想这件事吧。”她把头顶在栅栏上,喘了一忽儿,轻轻的沙沙的说道:
“听我爸爸说,我家祖先,从福建坐上木头帆船,什么机器也没有,光有一个指甲大的指南针,就飘过大海,到台湾来了。我常常梦见这么条船。”“我也做了个梦了,也梦见一条船。船上有许多人,有你,有我。这船开到大陆,我这个地理教员带你逛上海,杭州,……”
她浑身一松,低下头,快要伏在地上了:
“我也做过跟这一样的梦。”忽然直挺挺跪了起来,把两手伸出栅栏,我也赶快伸出两手。我们隔着栅栏紧紧握着,她的眼角有一颗泪珠,可又静静笑着说:
“我们到北京,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了,你说,你快活不快活?快活不快活?”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升起,万物苏醒。
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说完了故事,迟疑了半天,静静笑道:“什么样的性格呀!”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林斤澜(1923—2009),男,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温州市。1950年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任文学创作组成员,创作小说、剧本等多种。代表作品有 《春雷》、《飞筐》、《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等。一生经历丰富,创作颇丰,曾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
【请思考】这篇小说是林斤澜的成名作,体会他的写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