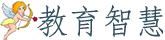奈保尔冰与火——我读《布莱克·沃滋沃斯》
一
一个诗人,沃滋沃斯,他穷困潦倒,以讨乞为生,一直梦想着完成他最伟大的诗篇,而最终,他孤独地死去了。 ——这就是《布莱克·沃滋沃斯》,是《米格尔大街》的第六篇。
比较下来,在小说里头描写诗人要困难一些。为什么?因为小说的语言和诗歌的语言不那么兼容。诗人有诗人特殊的行为与语言,诗人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让小说的腔调变得做作。当然了,小说的魅力就在这里,麻烦的地方你处理好了,所有的麻烦将闪闪发光。
奈保尔是怎样处理这个麻烦的呢?铺垫。——你沃滋沃斯不是一个乞丐兼诗人么?你沃滋沃斯不是很特殊、不好写么?那好吧,先铺垫。只要铺垫到了,无论沃滋沃斯怎么“特殊”,他在小说里头都不会显得太突兀、太做作。
什么是铺垫?铺垫就是修楼梯。二楼到一楼有三米高,一个大妈如果从二楼直接跳到一楼,大妈的腿就得断。可是,如果在二楼与一楼之间修一道楼梯,大妈自己就走下来了。奈保尔是怎么铺垫的?在沃滋沃斯出场之前,他一口气描写了四个乞丐。这四个乞丐有趣极了,用今天的话说,个个都是奇葩。等第五个乞丐——也就是沃滋沃斯——出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特殊”,他已经不再“突兀”,他很平常。这就是小说内部的“生活”。
铺垫的要害是什么?简洁。作者一定要用最少的文字让每一个奇葩各自确立。要不然,等四个人物铺垫下来,铺垫的部分将会成为小说内部巨大的肿瘤,小说将会疼死。我要说,简洁是短篇小说的灵魂,也是短篇小说的秘密。
我们来看看奈保尔是如何描写第三个乞丐的,就一句话——
下午两点,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引路,来讨他的那份钱。
非常抱歉,我手头上所选用的《米格尔街》是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的。但是,我记忆中的另一个版本叫《米格尔大街》,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翻译,同样是一句话——
下午两点,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引路,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
我不懂外语,我不知道哪一个翻译更贴紧奈保尔的原文,也就是说,我不可能知道哪一种翻译更“信”,但是,作为读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个翻译,第二个翻译“雅”。道理很简单,“来讨他的那份钱”只描写了一个讨乞的动作,而“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却有了一个乞丐的性格塑造,——这个盲人太逗了,真是一朵硕大的奇葩,他近乎无赖,天天来,天天有,时间久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乞丐了,他可不是“讨”饭来的,人家是执行公务。这个公务员很敬业,准时,正经,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他气场强大,来了就取,取了就走。这样的正经会分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幽默,促狭、会心、苦难、欢乐,寓谐于庄。美学上把“寓谐于庄”叫作滑稽。这才是奈保尔的风格,这才是奈保尔。所以,第二个翻译不只是“雅”,也“达”。
补充一句,美学常识告诉我们——
内容大于形式叫悲壮。——内容太大,太强,太彪悍,形式裹不住内容了,形式就要撕裂,就要破碎,火山就要爆发,英雄就得牺牲,这就是悲壮,一般来说,悲壮的英雄都是在面临死亡或业已死亡的时候才得以诞生;
内容等于形式呢?它叫优美。——它般配,安逸,流畅,清泉石上流,关键词是和谐。大家都知道“和谐社会”这个词,什么意思知道吗?是指“人”这个内容与“社会制度”这个形式高度吻合,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面,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自身的幸福,就像《新闻联播》里头常见的那样,乡亲们都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至于形式大于内容,那就不妙。是内容出现了亏空,或者说,是形式出现了多余。猴子的脑袋不够大,人类的帽子不够小,这就沐猴而冠了。“沐猴而冠”会让我们觉得好笑,这个“好笑”就是滑稽,也叫喜,或者叫作喜剧。喜剧为什么总是讽刺的?还是你自己招惹的,你出现了不该有的亏空。亏空越大,喜剧的效果越浓,所以讽刺从来离不开夸张。所以啊同学们,做人要名副其实。你不能吹牛、不能装,一吹牛、一装,形式马上就会大于内容,喜感即刻就会盯上你。就说写作这件事,假如你只写了几部通俗小说,借助于炒作把自己包装成纯文学作家,那就沐猴而冠了,就会成为喜剧里的笑柄。我常说,说实话、不吹牛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
——回到小说上来,乞丐可以来“讨”,乞丐也可以来“取”。你看看,小说就是这样奇妙,也就是一个字的区别,换了人间。
既然说到了翻译,我在这里很想多说几句。你们也许会偷着笑,你一点外语都不懂,还来谈翻译,哪里来的资格?我告诉你,我有。我是汉语的读者,这就是我的资格。——看一篇译文翻译得好不好,在某些特定的地方真的不需要外语,你把小说读仔细就可以了,我现在就给你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的译本很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是一篇书信体的小说,自然就有一个收信人的称呼问题。关于称呼,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事实上,写信的女人和读信的男人是什么关系?是情人关系。不只是情人关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男人的情人太多了,他狗熊掰棒子,已经认不出这个写信的女人了。然而有一条,不管这个男人还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是“素昧平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你)见过多次、却已经不再认识(我)我特地把北京大学张玉书教授的译本拿过来比对过一次,尽管我不懂德语,可我还是要说,张玉书教授的翻译才是准确的。——我这么说需要懂外语么?不需要。
第二个例子来自《朗读者》,作者施林克。它的译本同样众多。在小说的第四章,女主人公汉娜正在厨房里头换袜子。换袜子的姿势我们都知道,通常是一条腿站着。有一位译者也许是功夫小说看多了,他是这样翻译的——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面对“一条腿站立”这个动作,白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金鸡独立”呢?老实说,一看到“金鸡独立”这四个字我就闹心。无论原作有没有把女主人公比喻成“一只鸡”,“金鸡独立”都不可取。它伤害了小说内部的韵致,它甚至伤害了那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我说这话需要懂外语么?不需要的。
现在,布莱克·沃滋沃斯,一个乞丐,他来到“我”家的门口了。他来干什么?当然是要饭。可是,在回答“我”“你想干啥”这个问题时,他是这么回答别致了:“我想看看你们家的蜜蜂。”
在肮脏的、贫困的乞讨环境里,这句话是陡峭的,它异峰突起,近乎做作。它之所以显得不做作就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四朵奇葩。我们仔细看看这句话,行乞是一个绝对物质化的行为,“看蜜蜂”呢,它偏偏是非物质的,属于闲情逸致。这是诗人的语言,肯定不属于乞丐。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沃滋沃斯的另一个身份,诗人。
可是,我们再看看,这个诗人究竟是来干啥的——
他问:“你喜欢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喜欢。”
他从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有铅字的纸片,说:“这上面是首描写母亲的最伟大的诗篇。我打算贱卖给你,只要四分钱。”
这是惊心动魄的,这甚至是虐心的。顽皮,幽默。这幽默很畸形,你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笑出声来,你的眼泪就出来了,奈保尔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当奈保尔打算描写乞丐的时候,他把乞丐写成了诗人;相反,当奈保尔打算刻画诗人的时候,这个诗人却又还原成了乞丐。这样一种合二而一的写法太拧巴了,两个身份几乎在打架,看得我们都难受。但这样的拧巴不是奈保尔没写好,是写得好,很高级。这里头也许还暗含着奈保尔的哲学:真正的诗人他就是乞丐。
如果我们换一个写法,像大多数平庸的作品所做的那样,先用一个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乞丐的身份,再用另一个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诗人的身份,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那样写不好。啰唆是次要的,关键是,小说一下子就失去它应有的冲击力。
“只要四分钱”,骨子里还隐藏着另一个巨大的东西,是精神性的,这个东西就叫“身份认同”。沃滋沃斯只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却绝不认同自己的乞丐身份。对沃滋沃斯来说,这个太重要了。它牵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尊严。在《布莱克·沃滋沃斯》里头,奈保尔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过“尊严”这个词,但是,“尊严”,作为一种日常的、必备的精神力量,它一直荡漾于小说之中,它屹立在沃滋沃斯的心里。
所以,从写作的意义上来说,“只要分四钱”就是沃滋沃斯的性格描写,这和“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个短篇小说总共只有七章。在第二章的开头,作者是这样写的——大约一周以后的一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米格尔街的拐弯处又见到了他。
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啦。”
我问:“卖掉诗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我院里有棵挺好的芒果树,是西班牙港最好的一棵。现在芒果都熟透了,红彤彤的,果汁又多又甜。我就为这事在这儿等你,一来告诉你,二来请你去吃芒果。”我非常喜爱这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非常家常,属于那种生活常态的描写。但是同学们,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段文字,我是不会给大家讲解这一篇小说的,这一段写得相当好。
第一,我首先要问同学们一个问题,这一段文字到底有没有反常的地方?如果有,在哪儿?
反常的地方有两处。一、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乞丐都是上门去找别人的,可是,沃滋沃斯这个乞丐特殊了,他牺牲了他宝贵的谋生时间,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二、乞丐的工作只有一个,向别人要吃的,这一次却是沃滋沃斯给别人送吃的。你看,反常吧?
不要小瞧了这个反常,从这个反常开始,沃滋沃斯的身份开始变化了,他乞丐的身份开始隐去,而另一个身份,孤独者的身份开始显现。也就是说,沃滋沃斯由诗人+乞丐,变成了诗人+孤独者。无论是乞丐还是孤独者,都是需要别人的。
我感兴趣是,这个反常怎么就出现了的呢?有原因么?如果有,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原因就是一句话,是“我”的一句问话,“卖掉诗了吗?”
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基础。沃滋沃斯是谁?一个倒霉蛋,一个穷鬼,一个孤独的人,在这样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有人搭理他么?有说话的对象么?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回看第一章,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整整第一章都是沃滋沃斯和“我”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沃滋沃斯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他发现“我”也是一个诗人,并且像他“一样有才华”。这当然是扯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敏锐的、情感丰富的诗人发现了一样东西,那个孩子,也就是“我”,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这个宝贵的同情心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立即得到了证实:一见面,孩子就问,——卖掉诗了吗?对沃滋沃斯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呢?没有了。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他在路边等“我”一点也不反常。这一老一少彼此都有情感上的诉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布莱克·沃滋沃斯》是一篇非常凄凉的小说,但是,它的色调,或者说语言风格,却是温情的,甚至是俏皮的、欢乐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奈保尔的魅力就在于,他能让冰火相容。
第二,沃滋沃斯不去要饭,却在那里等“我”、邀请“我”,为的是什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当然请“我”吃芒果。让我们来注意一下,那么简洁的奈保尔,怎么突然那么啰唆,让沃滋沃斯说了一大堆的话。这番话呈现出来的却不是别的,是沃滋沃斯和一棵芒果树的关系,什么关系?审美的关系。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一段的,这一段在我的眼里迷人了,一个潦倒到这个地步的人还如此在意生活里的美,还急切地渴望他人来分享美,它是鼓舞人心的。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审美是艺术上的事,是艺术家的事,真的不是。审美是每一个人的事,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审美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藏着价值的系统与序列。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如果因为贫穷我们在心理上就剔除了美,它的后果无非就是两条:一、美的麻木;二、美的误判。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的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
奈保尔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贫困、肮脏、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社会景区,但是,这贫困、肮脏、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真正绝望过。正如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它证明了“绝望的不存在”。它生机勃勃,有滋有味,荡气回肠,一句话,审美从未缺席。这个太重要了。这**一点也不悲壮,相反,很家常;你看看沃滋沃斯,都潦倒成啥样了,讨饭都讨不着,他在意的依然是一棵树的姿态。
第三,而事实上,在这段文字里,“西班牙港最好的”芒果树其实不是树,是爱情。就在第二章里,有一段沃滋沃斯的追忆似水年华:“姑娘的丈夫非常难过,决定从此再也不去动姑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于是,花园留了下来,树木没人管理,越长越高。”文学界流行一句话,爱情不好写,这是真的,爱情从来都不好写,我到现在都害怕描写爱情。可我要说,在这篇小说里头,爱情的描写太成功了,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九行。然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感,有足够好的记忆力,我们在阅读这一段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突然会醒悟,会联想起前面有关“等待”的那段话:天哪,难怪沃滋沃斯要在那里等待孩子,难怪他要请孩子去看芒果树,难怪他要让孩子去吃芒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爱情。他要看着孩子吃掉那些“红彤彤”的芒果,他要看着蜜汁一样黏稠的果汁染红孩子的“衬衫”。看出来了吧,奈保尔对爱情的描绘绝对不是短短的九行,从“等待”就开始了。所以,好读者不能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好读者一定要会联想。——奈保尔让沃滋沃斯等待“我”的时候描写爱情了么?没有。都藏在底下了,这就是所谓的“冰山一角”。从小说的风格上说,这就叫含蓄;从小说的气质上说,这就叫深沉。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的气质,好的小说一定是深沉的。你有能力看到,你就能体会这种深沉,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反而有勇气批评作家浅薄。
我在这里罗列了第一、第二、第三,特别地清晰。可我要强调一下,这是课堂,是出于课堂的需要,要不然你们就听不清楚了,——但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误解,以为作家的创作思维也是这样的,先备好课,再一步一步地写,还分出一、二、三、四,不是,绝对不是。那样是没法写小说的。我想你们都知道,讲小说和写小说不是一码事。在写作的时候,作家的思维要混沌得多,开放得多,灵动得多,深入得多。有一种思维模式叫作直觉,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是非理性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心机制,有时候,它甚至就不是一种思维。很抱歉,这个我就说不好了。说不好也好办,我们就把那种内心的动态叫作天赋吧。天赋就是他知道该怎么写。
对了,因为我来了南京大学,经常有记者问我,写作到底能不能教?当然能教,我现在就在教你们。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天赋是没法教的,我自己都没有天赋,如何去教你们?可是,我依然要强调,只要你热爱,用心,用脑子,再有一个好老师,你自己就有能力挖掘自己的天赋,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这一点我一丝一毫也不怀疑。我同样不怀疑的还有一条,你不用心,不用功,不思考,不感受,不训练,那你哪怕是莫言,最终也只能是闭嘴。
也许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祛魅,不要刻意地神化天赋。神化天赋是一些人的虚荣心在闹鬼,别信。你们要相信我,天赋是可以发掘的,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直到你吓了自己一大跳。
小说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差不多是雷同的,只写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沃滋沃斯的现实之痛。这个现实之痛并不是沃滋沃斯吃不上饭,而是沃滋沃斯始终没能把“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给写出来。而事实上,我说这三章是雷同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它们的区别其实很大,分别代表了沃滋沃斯几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唯一雷同的是小说的方式,差不多全是对话,也就是沃滋沃斯和“我”的对话。关于这个部分,我由两点要说。
一、对话。
对话其实是小说内部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一种表述方式,许多初学者误以为它很容易,就让人物不停地说,有时候,一部长篇能从头“说”到尾。这样的作品非常多。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是聂华苓的故事。聂华苓六十年代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五十多年了,用英语写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她一直用汉语写。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用英语写作呢?用汉语写还要翻译,多麻烦哪。聂老师说不行,她尝试过。用英语去描写、去叙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写到人物的对话,穿帮了,美国的读者一眼就知道不是母语小说,而是用外语写的。
听了这番话我很高兴。我在实践中很早就意识到对话的不易了,——对话是难的,仔细想一想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里头有一个小说人物与小说语言的距离问题。描写和叙述是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它们呈现着作者的语言风格,它离作家很近,离小说里的人物反而远。对话呢?因为是小说人物的言语,是小说的人物“说”出来的,这样的语言和小说人物是零距离的,它呈现的是小说人物的性格,恰恰不是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作家很难把控,它其实不在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你很难保证这些话是小说的人物说的,而不是来自作家。许多作品如此热衷于对话,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对话写得好,而是因为作者在叙事与描写方面不过关,没才能,怕吃苦,想偷懒,回头一想,嗨,那就用对话来替代吧,多省事呢。这样的对话其实不是对话,而是规避描写与叙事。老实说,我至今都看不上从头到尾都是对话的小说。从头到尾都采用对话,写写通俗小说是可以的,纯文学肯定不行,纯文学有它的难度要求,对对话也有特殊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就以为对话很好写。罗曼·罗兰写小说已经功成名就了,后来写起了话剧,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练习写对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多次请我写话剧,包括林兆华导演,我一直没答应。许多人都批评我,说我太傲慢了。我哪里是傲慢哪,上帝,我是没那个本事。千万别以为小说写得好对话就一定写得好,每个作家都要扬长避短的。
二、诗人之痛。
我对诗人之痛特别有兴趣,因为我喜欢李商隐的诗。这个李商隐呢,和沃滋沃斯一样,也是一个痛苦了一辈子的诗人。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诗歌史翻出来看看,从屈原,到王粲,再到庾信、李白、柳宗元,一路捋下去吧,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李商隐之痛”,就像北岛所说的那样,“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猫头鹰”。——就在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上,陆建德老师说过一句话,巧了,李敬泽老师也在这个座位说过一句话,两位老师的话是一样的。两位老师说,中国的诗人都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头,说不出口:
我痛苦啊,到现在都当不上宰相。
在座的同学如果当时也在场,你们一定还记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美妙的是,辉煌的中国诗歌史是由一代又一代官场的失败者写成的。这个太独特了。他们痛苦,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下,他们很少因为他们的诗歌而痛苦,除了那个倒霉的贾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诗人都有自己“李牛党争”,他们都在这个夹缝里,他们生不逢时的痛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李商隐最为著名的两句诗,太典型了,太有代表性了。这个“万丈才”指的是什么,这个“未曾开”又意味着什么,我想在座的都懂。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足以令人窒息的郁闷与痛苦偏偏和诗歌无关,虽然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喜欢沃滋沃斯的痛苦,我这样说不是幸灾乐祸,千万不要误会哈,这个你们懂的。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诗人,沃滋沃斯的痛苦和面包有关,和爱情有关,和孤独有关,和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有关,但是,和“万丈才”无关,和“未曾开”无关。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毕业生,是奈保尔让我看到了另一种“诗人之痛”,他丰富了我,他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感谢奈保尔。
小说到了第六章了,不幸的事情终于来了,沃滋沃斯死了。在沃滋沃斯临死之前,他把“我”搂在了怀里,对“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现在你听我讲,以前我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少年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出来的。还有那些什么作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我一直在反复强调,这是一篇凄凉的小说,但同时也是一篇温情的小说。我还说,奈保尔始终在塑造沃滋沃斯的性格,自尊,现在我必须要加上一条了,善良。
如果你们一定要逼着我说出这篇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我只会说,同情。但“同情”这个词恰恰又是危险的,它很容易和施舍混合起来,这里头当然也包括精神上的施舍。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同情和施舍无关,仅仅是感同身受。——你千万不要为我痛苦。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不是。我想谈的反而是另一个东西,历史观。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历史观里头,有一个大恶,我把它叫作“历史虚荣”。糟糕的文化正是“历史虚荣”的沃土。“历史虚荣”可以使一个人无视他人的感受、无视他人的生命、无视现实的生命,唯一在意的仅仅是“历史将如何铭记我”。它的代价是什么?是让别人、让后来的人,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我死了,可我不能让你舒服。常识是,“历史虚荣”伤害的绝不是历史,一定涵盖了现实与未来。
现在我想来谈一谈小说的面。只要一说起小说的“面”,我们很容易想起福斯特和他的《小说面面观》。那是一部教人如何阅的顶级教材。我没有福斯特的能力,讲不了那么全面,我现在所说的面是小说的层面。这个问题挺要紧的,属于小说的技术,这个技术不只是对阅读要紧,对写作也一样要紧。
无论阅读什么样的小说,哪怕是现代主义小说,我们首先要找到小说的一个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是由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小说的叙事空间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不管你的小说如何上天入地,小说必须回到这个基本层面上来,在这个层面上发展,在这个层面上完善,否则小说就没法写,也没法读,那就乱了套了。
在《布莱克·沃滋沃斯》这部小说里,一共有几个层面呢?四个,我们一个一个说。
在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小说的基础层面,总共有四个人物。一、“我”;二、沃滋沃斯;三、“我”母亲;四、警察。这四个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头。小说是以“我”和沃滋沃斯做主体的,那么,奈保尔为什么要涉及“我”母亲和那个警察呢?道理一说就通,母亲与警察构成了小说的背景,是他们构成了小说内部冰冷的文化氛围。关于那个警察,小说里一共只有两句话,但是,有和没有,区别是巨大的。
第二个层面本来不存在,但是,由于小说技术上的需要,奈保尔必须在沃滋沃斯出场之前为他做铺垫,这一来第二个层面就出现了,也是由四个人构成的,第一个乞丐,第二个乞丐,第三个乞丐和第四个乞丐。这个层面来自作者,属于作者的叙事层面。
第三个层面来自沃滋沃斯的钩沉,是沃滋沃斯的一段爱情。只有一个人物,当然是那个“酷爱花草树木”的姑娘。这个层面绝对不能少,它决定了小说的纵深,它影响并决定了第一层面里头沃滋沃斯的一切,行动,还有语言。如果没有这个层面,用黑格尔的说法,沃滋沃斯就不再是“这一个”沃滋沃斯。理论上说,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这一个”,否则,他就会游离,缺氧,从而失去生命。
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第四个层面。大家想一想,这个小说有没有第四个层面?有的。第四个层面来自姑娘的腹部,人物也是一个,就是“死在姑娘肚子里”的“小诗人”。从小说的结构来讲,有没有这个层面都不会影响小说的大局,但是,就情绪而言,这一个层面又是重要的,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锥子,一直插到沃滋沃斯心脏的最深处。
最后我们要谈的依然是一个技术问题,结构。说起结构,问题将会变得复杂。长篇有长篇的结构,中篇有中篇的结构,短篇有短篇的结构。我一直说,长、中、短不是一个东西不同的长度,而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三个不同的文体。一般来说,作家都有他的局限、他的专擅,很难在长、中、短这三个领域呼风唤雨。奈保尔是一个例外,他几乎没有短板。这是很罕见的,这是我格外喜欢奈保尔的一个重要原因。
短篇小说的结构又要细分,故事类的,非故事类的。如果是故事类的,还要分,封闭结构,开放结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统统不谈。我们今天只讲短篇小说非故事类的结构。
《布莱克·沃滋沃斯》是标准的、非故事类的短篇,严格地说,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和传记不同的是,它添加了一个人物,也就是“我”,这一来,“我”和小说人物就构成了一个关系。对小说来说,人物是目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依仗的却是关系。关系没有了,人物也就没有了。关系与人物是互为表里的。
那好,《布莱克·沃滋沃斯》就是一个人物传记,它没有故事,如何去结构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写这样的小说不能犯傻,去选择什么线性结构,那个是要出人命的。放弃了线性结构,如何结构呢?当然是点面结构。事实上,奈保尔所选用的就正是点面结构。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作品,你让奈保尔采用线性结构,奈保尔也无能为力。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有年轻人问我,点面结构的作品如何去保证小说结构的“完整度”呢?
先来听我讲故事吧。电影这个东西刚刚来到拉美的时候,拉美的观众很害怕:银幕上的人物怎么都是大脑袋?身体哪里去了?这个细节在《百年孤独》里头就有所展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反过来问,电影摄影师为什么只拍演员的脑袋?他凭什么把演员的身体给放弃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他创立了格式塔理论,也叫完形心理学。
完形心理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认知上的惊天大秘密,那就是,我们在认知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次序的问题:先整体,后局部。拿看电影来说,只要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个大脑袋,我们的脑海里立即就会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滴血的、搬了家的大脑袋。这不是由镜头决定的,是由我们的认知决定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做前提,摄影师才敢舍弃演员的身体,只盯着这演员的大脑袋。
——我们都知道“盲人摸象”这个笑话,这个笑话的基础是什么?是盲人的认知里头根本没有大象这个“完形”。对任何一个健全人来说,一看到象牙就可以看到大象,但是,对盲人来说,他们不行,在他们的巴掌底下,大象只能是一柄由粗而细的长矛。
回到小说,如果你想写一个传记性的人物,他总共活了98岁,你要把98年统统写一遍么?那就傻帽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线性的完整性,它可以是断裂的、零散的。甚至可以说,它必须是断裂的、零散的,仿佛银幕上舍弃了身体的大脑袋。你只要把大脑袋上的眼神、表情给说好了、说生动了、说准确了、说具体了,永远也不要担心读者追着你去讨要人物的大腿、小腿和脚丫子。——非故事类的短篇就是这样,结构完完整整的,未必好,东一榔头西一棒,未必就不好。
兄弟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学们批评。小说阅读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们看法没有真理性,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欢迎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
2015年9月17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