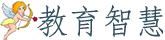3
洪梅北上入学那年,秋天来得早,九月刚过,风就凉了,不多日,校园里的银杏叶由绿转黄,梧桐叶跟着飘零了。宿舍窗外恰对着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路很宽,两旁种着高大的银杏树。洪梅没事就在这条路上徘徊,如同田野里拾稻穗的小女孩,入神地凝望着满树金黄,时不时俯身挑挑拣拣,盼着找出那片完美无瑕的落叶来。可是比来比去,捡起丢下,往往没个结论。一些在校园里混成了油条的男学长从她身旁路过,几步一回头,有的还嘬起嘴来吹口哨,极力想引她注目。她对这些轻佻的男生十分反感,从来不曾望过他们一眼。
不过,捡银杏叶的举动还是给她带来了艳遇。有一天傍晚,洪梅下了课回宿舍去,见楼下那条银杏道变了样儿:每棵树都甩光了叶子,白花花的枝条在风中摇曳着,几个鸟巢被高高地擎在空中,显得孤零零的,铺了一地的落叶被扫成了一堆又一堆,全然没了光彩,宛如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恍然一梦,化作待清理的垃圾了。她有点触景生情,联想自己身处新环境,老师同学还不熟,不知未来何去何从,就又想起了一年多前下葬的母亲。每当想起洪太太,她就站在现实的洪流之中——她用力地告诫自己,要坚强,要擦亮双眼,要有的放矢。
就在她驻足冥想的片刻,吱的一声,金属摩擦发出的尖叫把她吓了一跳。她条件反射般地扭过头去,一脸惊讶与茫然……原来,有个骑自行车的男生突然在她身旁急刹车,两条长腿支在地上,正抿嘴冲着她笑,老熟人似的望着她。
她连忙低下头去,脸变得红润了。
那男生不慌不忙地卸下背上的书包,抽出一本薄薄的书来,递到她眼皮底下,示意她接过去。
她抬起头来,羞红了脸,拿清澈的眼神望着他,并不回应他的要求。虽然经历了丧母之痛,她的傲气被抹杀了大半,但她绝不叫内心的尊贵有损半分。更何况,在不相识的男生面前,多一分矜持多一点胜算。我们知道,她在小学已经上过这一课了。
那男生有点不好意思了,缩回递书的手,将书托在胸前,用清脆响亮的声音自我介绍道:“我叫刘之童,咱们一个系,我比你大一级。我是成都的,改天请你吃火锅吧……”
洪梅静静地望着他,倾听着,不言语,仿佛要透过他那音乐般的声音识别他的心灵编码。
他见洪梅不搭话,有些意外,赶紧换了话题,说:“那天迎新,我见到你了,你叫洪梅吧。可惜我那天有事,没帮得上忙,很抱歉。你喜欢银杏叶,我也挺喜欢的,去年和今年各收集了一些,你想看看吗?”
他又把那本书递了过去。
洪梅这才看清了那书上印着“现代诗歌欣赏与创作”几个大字。她礼貌地接过书来,向刘之童点头致意。刘之童心想大功告成,要谢的反而是他,兴奋得语无伦次,赶紧道了别走了。
这个刘之童,长得又高又帅,挺入洪梅法眼。她坐在宿舍里将他猜测了一番,才翻开了那本谈诗的书。书里零零星星夹了些银杏叶,枯萎得厉害的是去年的,一片片无精打采,好像是些平面的木乃伊;另一些尚有水分的是今年的,同样被压得平平整整,但好歹还透着点生命的余辉。看来,失去了营养供给的叶子,越收藏越残废,假如趁早把它们丢进土壤里,还能做点肥料,储着惜着倒成了生命无常的见证了。
洪梅把那些叶子夹回了书中,仿佛把一具具尸体送回到棺材里,不禁愣了会儿神,才想起该浏览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免得刘之童问起。他既然用的是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就说明他别有用意。但是她刚看了两页,就怎么也读不下去了。古代那些诗,她读读还可以,总要应考,不背也不行;至于现代诗,她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尤其是那些恣意想像的诗句,她看了简直要作呕。现在班上有个男生偶尔写点堆满了词藻的散文诗,从头到尾虚无缥缈,不知所云,还拿到班上去传阅,洪梅只读了一个开头,便觉得胃疼。有个教授曾在课堂上动情地朗诵,“风与雨在海洋里,野鹿死在我心里。看,秋梦展翼去了,空存这委靡之魂”,她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来一见到那个浑圆矮胖的现代诗专家,就慌张起来,连忙退往后排,恨不能把自己藏起来。
假如刘之童的职业梦想就是作诗的话,那么他就是个再伟大的诗人,她也陪伴不起。不出三个月,洪梅就印证了这一点。刘之童潮水一般涌入她的眼帘,又潮水一般迅速退去。他三岁背三字经,四岁背唐诗,五岁背宋词,七八岁就背下了许多现代诗。父母虽一介平民,在当地小学教书,但教育意识却出奇地强烈。他们对诗并无特别的感情,只是信奉早教那一套,因此从儿子呱呱坠地起,就紧着时间督促他背书,至于背完就能写,他们倒不敢指望,但总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的道理。刘之童又从小背得溜,人人赞不绝口,他也就对自己爱诗且有作诗天分深信不疑。要是没了诗,他的生活就虚空了,人们该从哪个角度来认识他呢?他还是他本人吗?不,他将失去他的招牌他的存在感。如同那些以各类艺术特长立足于同龄人之间,甚至以此鹤立鸡群的同学,难道他们有朝一日敢把证明自己身份的武器丢开,把它踩烂,再用另一种方式去重塑自己?不,除非走投无路。不过,刘之童是个乐天派,又一直活在掌声之中,假如没有第一只黑天鹅出现,他对世上只有白天鹅的信念是毫不动摇的。如今他正站在试飞的舞台上,信心满满,一面读诗,一面写诗,还煞费苦心地为洪梅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可是洪梅没有一句看得懂的。那些诗的用词,浪漫,夸张,诡异,或许是随心所欲,因为词与词连缀成句后,超越了语法规范,大大挑战了洪梅的理解力。洪梅起初深受这预备诗人的爱情打动,想逼着自己去学点诗,哪怕只是鉴赏,但终究坚持不下去,就只好跟刘之童分道扬镳了。
其实,刘之童倒是个明理之人,他并不要求洪梅一定要研究诗,只要她能在一旁支持他就行了。他俩又同乡,颇有共同语言,生活习惯大同小异,而他又是个典型的四川男人,体贴入微,甘愿为女人所驱使。但是洪梅对婚姻的要求远比这高,至于谈谈而已,恋爱对象未必是结婚对象,这一点她是不赞成的。她怕浪费时间,错过韶光年华。所以,她讲究效率,希望快点给自己一个“成”或“不成”的答复。
有一天,她听说网上有种“作诗机”,只需按要求输入几个词,软件就能自动帮你完成一首诗。洪梅就拿这种机器诞下的一首诗去请教刘之童,刘之童不明就里,欣喜若狂,竟把这诗的“作者”当成他所崇拜的偶像。洪梅的心便冷却了,当机立断提了分手。刘之童恋恋不舍,如同画家失去了千年一遇的女模特儿,悲戚之极给了她一句慷慨赠言:“我情愿把光明给你,把黑暗留给自己!”洪梅觉得受之有愧,哪料得他竟一语道破天机。再怎么说,刘之童是她用心付出感情的头一个男生(或许也是最后一个),分手虽是她提的,她心里也万分难过。她便把这句话牢牢刻在了心底。
往后,洪梅觉得有必要排除所有中文专业的男生,她坚决拒绝他们身上那股酸文假醋味儿。她将目标对准理工科,本硕博均可,贫富不论,高矮不限,当然各方面条件越好越好。头一年里,班上流传着一句话,“肥水不流外人田”,文科系女多男少,但漂亮女生总该由自己人占了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男生追一个不成换一个追,动作快且不吃香的男生,甚至能把全班女生都追个遍。洪梅相貌出众,收到的求爱信息分外多些。不过,她一一谢绝了。凡婉拒不奏效的,她就直截了当地刺破他们的肥皂泡。男生之间消息灵通着呢,刘之童刚从她心上撤退不久,大家也都对她敬而远之了。女生中间总有些眼光实在的,与同班男生凑成了对儿,又从男友那里听来了对她不利的评论,想着自己牵手的正是被她淘汰下来的次等货,难免有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多半都对她起了偏见乃至敌意。
不过,洪梅并不太在意,她认为女性知己再多,也不及一个恰当的男友来得重要。她从没想过要在同性友谊方面创收,只是出于互帮互助的需要,在宿舍里不定期地表现得特别大方(她父亲与继母每个月都会给她寄一纸箱家乡的牛肉干或辣豆干之类的四川特产来,她有时刻意地藏着吃,有时则敞在桌面上,由大伙儿任意享用,怎么做全凭当时心情),定期地助人为乐(她养成了从不翘课并一字不落地抄下各科讲义的习惯,每到期末就将笔记借给大伙儿复印,考前两周与大伙儿一同熬夜背诵,共渡难关),所以室友们对她还是友好的。
室友中有个老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后,约了七个她从前的高中男同学来与她们宿舍“七仙女”(她们自称的)联谊,洪梅便又有了第二桩艳遇。这个男生名叫徐方波,父母均为大学教授,读的北科大机械自动化专业,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一头乌黑卷发与他的圆脸蛋配在一起,看上去像个滑稽可笑的驯兽师。不过,他不是滑稽,而是幽默。他志在必得,行事果断,刚见上面就当众约洪梅下周末上北海划船去。洪梅推脱有事,待他换过了几个时间,才应承下来。
这一回她提高了效率,只见了十来次面就把徐方波的追求之路堵上了。说实在的,徐方波是个脑筋极灵活的京痞子,大串儿大串儿的北京土话从他嘴里奔涌而出,就像滔滔江河势不可挡,看上去有气场,听起来很可乐。如果洪梅听不懂了问他,每聊上五分钟问上十次八次的不稀奇,他都会屁颠儿屁颠儿地解说起来。他眼界开阔,什么材料都读,读过的古典名著甚至比洪梅还多;动手能力又强,什么东西坏了,他三下两下就给修好了。总的来说,实干家一个。然而,他纵然有一千个优点,也抵消不了他那张损嘴时不时要犯的错误。
这个徐方波口才太好,包括讽刺他人的能耐。或许老北京人都有这种损人的天赋,以把人损得体无完肤为乐,而被损者则以还嘴为乐,双方你来我往斗起嘴来,其乐无穷。但洪梅适应不了这种逻辑,欣赏不来他对她句句鸡蛋里挑骨头的幽默感。她尝试了几次去“镇压”他的口舌,他一反省就深表歉意,决定悔过自新,可是下一回老毛病又犯。他照样口若悬河,说不尽兴不罢休,怎么也放不下他那挑刺儿的绝活儿。洪梅自知对他缺乏影响力,便毫不犹豫地终结了这段往来。
跟徐方波拉倒,洪梅一点也不难过,反倒觉得一身轻松。她不是感受不到徐方波实实在在的优势对她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她的潜意识里有种强烈的意志在左右她这么抉择。
接下来,洪梅又相继与本校或兄弟学校的几个男生交往过,但时间都不长。他们的面孔,洪梅倒是不在乎的,只要不丑就行;他们的综合素质,正是洪梅研究的重点,她用她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办法去考察这一点。有的男生没头没脑,连自己的前途都未盘算过;有的男生大男子主义,事事以自己的意见为主;有的男生心胸狭窄,大小花销都要AA制;有的男生软弱无能,动不动惊慌失措;有的男生总想着身体的接触,从不想着灵魂的交流……一样又一样性格的缺陷人性的弊端,摆在洪梅面前,就像满手花花绿绿的扑克牌,却没有一张派得上用场。她并非试图寻求某个完美的形象,而是坚决找到那个可以塑造的对象。然而,很遗憾,他们总给她一种“朽木不可雕”的感觉,总是叫她一次次地拿希望换失望。
做了许多无用功之后,她突然发现,她读大三了,她所剩下的宝贵时光不多了。如果她在这两年内,精确地说,一年半内(因为大四寒假之前就该决定自己的方向了),还没有将男友确定下来,毕业后可往哪里去?考研她没兴趣,留京工作一年比一年难,到外地去,那么多城市怎么选?而回老家,她绝不能接受,毕竟家里不是她母亲坐镇了,而是她的继母;继母待她再好,还是继母。
后来,她听说到某个高校论坛上“征友”,准定大丰收,便小心翼翼地拟了一篇巧妙的说辞,附上几张自己最得意的照片,上传了。果然,刚发完不到十分钟,她的电子邮箱就爆满了(那时候邮箱空间只有几兆)。她一整天坐在微机房里目不暇接地收信、读信、回信、删信,信件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简直扑天盖地,如雁群过境。她全神贯注,神经紧绷,收呀,读呀,回呀,删呀……一连三天,她累得眼睛快花了,身体快虚脱了,可是,她突然间单枪匹马面对这黑压压的罗马军团,即使身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指挥官,头一回上战场就得应付这海量的部众,也免不了乱了阵脚,管理不周。她害怕错过了合适人选,一封封仔仔细细地读,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照片看。凡是她觉得符合标准的,就给予几句答复,凡是她觉得没门的,就当即删掉。可是,她忘了对这些筛选下来的信件做个登记表,哪些人是头一次来信,哪些人是被删除了再次来信,哪些人是她答复了所以再次来信,她都对谁说过了什么,谁又回复了她什么,谁又对应了什么基本信息,她自己也迷惑了。那时候,电子邮箱功能有限,虽给了她一个好渠道,却把她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四五天后,那些应征者无一例外地被她得罪光了,再没有人给她写信。她由极度亢奋与疲劳,一下子转为极度悲观与绝望,于是三下五除二将所有信件清空了。
不料,一周后,她收到了三封奇特的信。
一封自称“垂垂老矣”,似乎已近风烛残年。他祖籍安徽,拥有美国绿卡,无奈原配夫人逝于海外,悲痛不已,于是携子归国。现任教于某高校,儿子随他在附近学校就读。
一封自称“尼采随从”,感慨世事无常,欲抓住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分一秒。他毕业于西安某高校,在京工作,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就在洪梅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敬请斟酌,恭候约见。
一封自称“恐龙”,又特别定义为“丑人王”,只怕见光死。他毕业于北大计算机专业,在一家外企搞技术研发,收入颇高,有房有车,然而自卑淹没了他追女孩儿的勇气。
洪梅有了许多失败的经历,反而不再急于求成了。她打算从最不可能成的那人见起,好让自己心里抱有希望——假如背后还有垫底的,人自然就能放开一些。她先给“丑人王”留了宿舍电话,“丑人王”当天就给她打来了,两人聊了好长时间,倒聊得投缘。那人声音浑厚有磁性,听起来蛮悦耳的。当晚洪梅恰好去北大旁听,他就住在那附近,于是两人约好晚上九点半在北大东门见面。孰料,洪梅左等右等,过了一个小时,那人还未出现。她穿了一条撒了银粉的绣花亚麻长裙,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一忍再忍,最终全身都快冻僵了,只恨不能从地上抓条裹尸布将自己卷起来。她怀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愤懑,追上了开往她的学校的末班车,在车上禁不住湿了眼。她这才想起上个秋天,她们宿舍曾和清华一个男生宿舍联谊,约好一同上圆明园秋游,那群男生竟然在会面地点躲了起来,等把她们七个女孩的相貌一一研究、鉴赏透了之后才现身。她们给那男生宿舍拨了许多通电话,无人接听,又见得一行七人突然幽灵般冒出来,才识破了内情,于是愤然离去……这些人!肤浅的无耻的视觉动物!连最起码的以礼待人的德行也没有!洪梅暗骂着,一颗心都快窒息了。
回到宿舍,“丑人王”来电话了,一万个道歉洪梅也不愿意原谅他了。他辩解有事爽约,但谁知道呢?当初那帮清华男生也有无数个理由证明自己无辜。
洪梅给自己的低落情绪放了数天假,才和下一个候选人约见。次可能成的,她认为是“垂垂老矣”。她倒不全然否定老夫少妻,她设想的是,假如对方事业有成,一切奋斗停当了,你投靠过去,除了享受还是享受,无忧无虑,甚至连生孩子的责任也免了,那不是捡了个大便宜?所谓“一树梨花压海棠”,她心上浮起苏东坡的诗来,眼前就现出了她继母年轻时的情景,禁不住嘴角一扬,乐了。
“垂垂老矣”约她在一家日本料理就餐。他慷慨解囊,破费了一桌好菜,请洪梅吃了个心满意足。可洪梅不知怎么的,就是不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他,甚至要找个话题和他交谈都有困难。她始终不敢把眼睛朝他脸上瞅,她实在无法想像自己跟一个皮肤松弛、皱纹显赫、又矮又瘦的老男,手拉着手,贴一贴脸,还要接吻!
那老男四五十岁,身子板薄,才越发显老。他看起来温文尔雅,善良宽厚。他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洪梅,欣赏一朵鲜花似的频频点头,不住地说“你的生活刚刚开始”,好像坐在面前的是他失而复得的女儿,而不是他要物色的用以替代亡妻的新欢。他自说自话地讲起,他喜欢逛街购物,喜欢买菜做饭,喜欢和大街小巷的小贩们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也是种生活的乐趣,不是吗?他问。
不!绝不!看谁去讨价还价了。女人讨价还价,比如洪太太和她,那是一种会持家的表现,可是男人讨价还价,就赤裸裸地表明他斤斤计较的本性了。纠缠于生活琐事又小肚鸡肠,过起日子来,处处紧巴巴的,当然目前这顿饭除外,可怎么拿得出手?她前面交往过一个男生,牙膏挤不出来了,他拿截钢尺一寸寸地抹过去,把整条牙膏管儿刮得纸一般薄,直把里头最后一丁点儿膏脂给追出来。她见了就来气!洪太太是个舍得消费的人,拿一个月工资买条毛背心都下得了手,哪至于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抠门?洪梅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挥金如土她还不敢想,但体面的优裕的生活她还是要的。她嘴上没有应答,心里却一环扣一环,立即推断这个老男太不合适。
这一次相亲又告失败,但洪梅心里快活了许多。她又受到了青睐,情绪再度高涨起来。第二天晚上,“尼采随从”加班回来,路过学校门口,他俩就在围墙外那排老槐树下见面了。
这个男人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身材高大,体魄强健,五官又生得有棱有角,看上去魅力十足。他那深沉的目光执着地望着洪梅的眼睛,好似一股暖流不顾一切地要往她的心灵里去。她的每个毛孔都感受到了这份深情,一身便都软化了。聊不过三五分钟,他就在夜色中将洪梅紧拥在怀里,拿脸贴着她的长发,仿佛苦等了十八年的王宝钏终于盼回了至爱。洪梅从未被一个男人这么大胆、热情地搂抱,心怦怦直跳,理智早吓晕过去了。她由着他拥吻,一层深似一层地吻。
时光悄悄地流走了,校门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他俩仍像两尊相拥而立的塑像,抱在一起热烈地贪婪地接吻,仿佛天地间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两条舌头拼命要融为一体的欲望。
两人终于吻够了,却发现洪梅无处可归了。“尼采随从”便邀请她一同回他的住所,并保证只做她愿意做的事,绝不对她有所强求。洪梅这才恢复了点理智,稍稍有了些清醒,一面回想起方才烈火干柴的激情,一面回想起一向遵循的谈情说爱的原则。这下可怎么办?她既没有找保安敲门回宿舍的勇气,又没有跟这个刚认识的男子回去的勇气。是的,宿舍里的女生比她要开放得多,她们闭了灯凑在一起看所谓的性教育视频,她们跟男友开房,假期悄悄地蜗居在男友宿舍里,她们兴高采烈地谈着那些爽歪歪的事情,而把洪梅的保守视为笑柄,有些外语专业的女生外语片看多了相当前卫,甚至在网上公然叫卖自己包月价位几何……可是这一切全是别人的生活,不是她洪梅计划中的项目。她只想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给自己的丈夫,哪怕婚前预支,也是不允许的。男人得到了就腻烦了,何况这个陌生人是她要找的另一半吗?她绝不会为了一时欢乐而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犹豫了半晌,“尼采随从”替她做了决定,牵着她的手走着回去了。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租的只是一套房里的一间。他急着去洗澡,洪梅便在他的小单间里看他出差到非洲的相册。他拍了许多非洲女人,黑黝黝的皮肤,肥大外翻的嘴唇,一个个袒胸露乳,有的正在劳作,有的正在休闲。其他的都是些女明星的明信片,多数是周迅的倩影。
他住的小房间实在小得压抑,除了一张旧书桌,就只搁得下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不过,那张书桌挺宽,靠墙一端摆着一列书,净是些深奥的哲学书,其中当然不乏尼采之作,另外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畅销书。洪梅坐在床上,手搁在桌上翻相册,然后翻书。她不喜欢晦涩难懂的伟大哲学,但好歹对爱智者有种由衷的敬意。抽一本,翻一翻,放回去;再抽一本……她得到的唯一有效的信息就是,他叫刘钰,他的名字写在某本书的扉页上。
刘钰换了一身干爽的睡衣紧挨着她坐下,轻声问她要不要洗澡。她摇摇头。他又打开相册,将一些非洲生活场景介绍了一番,然后谈起他喜欢的女明星。洪梅一言不发地听着,这些内容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她满脑子想的是,她要在这里安然无恙地度过一夜。刘钰百般劝说她躺好睡下,她就是不肯就范。刘钰保证不碰她,她才和衣进了被窝。但刘钰脱了衣服也钻进来了。洪梅心上一紧,只能不停地祷告。幸好,刘钰守着信用,并不对她怎样,只是时不时伸过脸去吻吻她;她反正被他吻过了,也就不在乎让他多吻几下了。
两人一夜无眠。刘钰克制得难受,在她耳边低语:“你有过经验吗?”“什么经验?”洪梅回问。刘钰叹道:“你真是个好女孩,我会好好珍惜你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又问:“我戴套套,可以吗?”洪梅不肯。“只是抚摸,好吗?”洪梅也不肯。刘钰软磨硬泡了一夜,竹篮打水一场空,天一亮,就送她回学校去了。
此后几天,刘钰每次下班都在校门口见洪梅,除了疯狂接吻,还带她去吃羊肉泡馍。然而,每次他约洪梅陪他回去,洪梅死活都不肯了。他口口声声地说“还像上次那样,什么也不做”,但是洪梅谨慎,害怕必有一失,坚决回绝。刘钰便在QQ上长篇累牍地劝说她,一个个小故事配着一个个大道理,但愿她能打开心门,迎他入住。他讲起他从前在西安与女友同居的往事,讲起他在情感上受过的创伤,讲起人生的变幻无常,讲起每个人该如何学会知足,学会行乐。但洪梅总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抵挡他的重重攻势,他最终沮丧了,激情瓦解了,在QQ上给她写了份最后通牒似的留言:
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
成为道德的行动本身不是道德的。使人们服从道德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奴性,虚荣,自私,阴郁的热情,听天由命或孤注一掷。服从道德,恰如服从一位君主,本身并无道德可言。
如果我们整天满耳朵都是别人对我们的议论,如果我们甚至去推测别人心里对于我们的想法,那么,即使最坚强的人也将不能幸免于难!因为其他人,只有在他们强于我们的情况下,才能容许我们在他们身边生活;如果我们超过了他们,如果我们哪怕仅仅是想要超过他们,他们就会不能容忍我们!总之,让我们以一种难得糊涂的精神和他们相处,对于他们关于我们的所有议论,赞扬,谴责,希望和期待都充耳不闻,连想也不去想。
纵使人生是一场悲剧,我们也要快乐地将它演完。
你说呢?
洪梅不知道这些话的出处(尼采作品的摘抄与拼凑,只有最后三个字是他自己的手笔),以为是刘钰的原创,反反复复将这些段落读了几十遍,上百遍,读得她泪眼模糊。她确信刘钰是个思想深邃的人,他的境界不一般,但她不确定他是不是可靠,更不确定他会不会和她结婚,而他的论调又悲观,口头上总挂着“无常”二字。说到底,除了他的吻技,洪梅实在想不出他的好处了。于是她狠一狠心,跟他一刀两断了。
一晃就到了大三下学期,两件事给了洪梅极大的震撼。一件是她目睹的,一件是她耳闻的。一天下了晚自习,她路过学校图书馆,竟然在图书馆侧门外,一条宽大的公路旁,撞见了一对男女学生在放纵地云雨。他们光着身子缠在一起,像两条交错盘绕的银蛇,在那一溜窄窄的路边草坪上激烈地翻滚,尽情地呻吟。几盏路灯将橘黄色的光投到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盖上了一层轻柔的纱。学生们三三两两从这里路过,并不多看一眼,好像人家在吃饭睡觉,观望是不礼貌的行为。洪梅却一阵心惊肉跳,飞一样地跑回宿舍去了。紧接着,她听说有个大四学姐聪明漂亮,追求者如云,可是她挑花了眼,最终被一位从新疆来京的流浪歌手骗去了财色。曾经有个留学澳洲的男生千里迢迢地跑过来,给她送了999朵红玫瑰,她请全宿舍女生一起修修剪剪,用这些花来装饰每个女生的床;曾经有个钻石王老五开着辆保时捷接送她,递给她一串房子的钥匙,她一笑置之;曾经有个同校男生为她叠了1000只千纸鹤,她婉拒了,那男生痛哭,她举起那个装着他的心愿的透明印花玻璃瓶摔了个粉碎……然而,一物降一物!当那个流浪歌手楚楚可怜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甘愿为他付出一切,与他同居,给他钱,两人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个流浪者借遍了她的同学好友的钱,不知所踪。
洪梅被这两则不搭杠的新闻吓了一跳,仿佛有人对她当头棒喝,逼迫她做出改变。我们便知道,她的命运就要为之转折了——
她马上就要遇上她愿意跟随一生的人,当然就是刘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