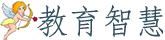1
转眼春节又快到了,这是一年一度熊孩子作乱高发的时期,各单位请尽快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普遍来说,熊孩家长,都是些个人素养有问题的人。实际上,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自己为人处世都很不错,娃却非常熊。
“惯娃=害娃”,谁不知道,到了执行层,家长表现就千姿百态。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首先很相信民主的亲子关系,也更容易自我怀疑。其次,他们的内心害怕管得太严会伤害娃。
7、8、90后的父母当中,很多自己小时候是在非常严厉地管教下长大的,他们曾经因为各种限制,非常痛苦。
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就特别提倡“爱和自由”,希望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多一些自由。因此,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选择从宽,导致娃不清楚边界在哪里。
当亲子关系处于下图中朋友型-孩奴型区间时,娃很容易做出熊孩行为。
这时的家长是完全没有权威感的,也就是在四种教养方式中的permissive style(放任型)。
2
家长没有权威感,对娃有什么坏处?
坏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娃特没安全感。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都顺着娃听娃,为什么娃还会没有安全感?
你想,娃基本上是一个天外来客,对地球上的规则一无所知。父母给他一切自由,想做啥做啥,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学前的娃,基本上很难预知做一件事即将产生的后果,所以很多决定,对他们来说,都太沉重了。
打个比方,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一家单位,董事长说:这是我们单位下半年的宣传方案,你来决定用哪个吧。你会不会特别惶恐?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方案有什么区别,会造成什么后果。
第二:外界对娃会有很多恶意,导致娃小小年纪就要承受压力。
娃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会不会直接来一顿胖揍?娃弄坏了表哥的收藏的玩具,家长没在场,表哥会不会偷偷折磨娃?如果娃在小区攻击别人家娃,对方爸爸会不会上来就一大耳光子?
百度下“怎么对付熊孩子”,就会知道,熊娃在很小的,心理完全没有承受能力的年龄,就会面对来自社会深深的恶意。是立刻学乖而将来人格健全,还是发展成反社会人格,可能得看熊娃运气。
家长以为是宽松,是给孩子更多自由和快乐,其实是害了娃。
3
那么,如果父母想要在孩子面前建立权威感,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建立权威感的基础。
一、父母自己要积极乐观,能做孩子的榜样。
孩子是高度能(欺)量(软)敏(怕)感(硬)的生物,本能上听从强有力的人。
有些妈妈整天抱怨:娃爸不做家务啊,婆婆苛刻啊,单位领导同事欺负啊……长期下来,娃也会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在欺负妈妈,妈妈是一个弱者,那还能指望娃听弱者的话,变成更弱的人吗?
所以父母首先要有积极乐观的人格,我说的不是那种外强中干的假装牛逼(典型表现为外面受气,回家揍娘们揍娃揍猫猫狗狗),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强大,遇事不抱怨。
作为父母,自身人格建设是很重要的!
二、不要把自己的心理阴影投射在娃身上。
有些父母小时候被家长和老师,压制得太过了。后来自己当父母的时候,孩子犯了错,明知该怎么处理,可就是“心软”没法“下手”。
其实,有些父母之所以“心软”,根本不是心疼孩子,而是产生了心理投射,看到了小时的自己。
可是,那时候的我们,跟现在的孩子,是同一个人吗?面临的是同样的处境吗?
根本不是。
因此,那些从小被压制的父母,在处理孩子的问题时,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现在我管教孩子,是在告诉他基本的社会规范,是为了他好。他不是当初的我自己,他并不可怜。如果我放任他为所欲为,才会真的害了他。
三、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做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的可怜人。
很多自我情绪管理没有经过训练的父母,自己遇到什么事儿就容易情绪失控。管教娃时,家长情绪就特坏事儿。
面对暴怒的父母,娃只能感觉到可怕,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大脑也一片空白,吓懵逼了。
家长也许会对娃解释问题所在,但沟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字面懂了,内心不一定懂,很多时候是多次沟通后,才真正意识到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往往需要跟娃对同一件事情反复沟通。
娃并没有真正理解时,家长觉得“讲道理”没用,于是一次次地发怒,亲子关系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青春叛逆期来的时候,亲子关系的问题就一起爆发了。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子女在成年后,只能泛泛地相处,但并没有真正的沟通。
因此,当家长要发怒时,一定要警告自己冷静后再处理。即使娃仍在不断哭闹,父母也可以什么话都不说,坐在孩子旁边,静静地看着孩子,直到自己冷静下来。
4
建立权威感,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根据娃的年龄和能力,给孩子自由,尽可能地具体。
娃能有多少自由,是跟他能承担的责任成正比的。能承担多少责任,就能有多少自由。
你可以这样想象,孩子的自由是一个圆圈。当孩子很小,比如一两岁的时候,她的自由很小,只是一个小小的圆;等他长到三四岁,这个圆圈扩大一点;到五六岁的小青春期,孩子自由的圆圈又扩大一点……慢慢地,到了孩子二十一二岁,就该给他全部的成人的自由。
每当孩子触碰边界,你就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让孩子回到他的圆圈内。
有个小男孩六岁,大概是小青春期的时候,很大声地跟我说话,还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偏要”。这个时候,我明白,这是孩子在试探我的边界,我需要更清晰地告诉他可以做什么,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不允许。面对娃的试探,我也没必要生气或者发怒,因为孩子的力量在变强,这是他成长的一种方式。
第二:七岁以下的娃,家长就是家长,没必要和娃做“朋友”。
很多家长,都认为要和孩子做“朋友”,跟孩子平等地相处。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跟一个几岁大的娃,行为能力和能承担的责任,都大不一样,谈什么平等?这样的平等有意义吗?
你不同意娃去游乐场,要娃去看望姥姥。娃说:“你不尊重我,我就是想去游乐场。”
第二天,你要出差,娃不许你去,“昨天你都不让我去游乐场,我不许你去出差”。
这算平等么?
家长就是家长,是为娃制定规则,明确地划清界限的人。准确地说,对学龄前的娃,家长是管理者,和娃不是平等的。
哪一个单位的领导,事事都跟下属平等?只能是人格上的平等和尊重,该做决定的时候,还得领导来。
第三:已经决定的事情,不要用疑问句去请示。
以前刚开始带孩子的时候,经常性地犯傻。
到了午饭时间,我总是去问:“宝贝,我们收拾玩具,去吃饭了好吗?”这个时候,娃只要一说“不好”,我就卡在那里了。
其实,午饭什么时候吃,根本是大人决定的,不用问,告知一下就可以了。大人觉得自己差不多决定了的事情,千万不要用疑问句。你又不是真的要他决定,问疑问句不是多此一举吗?
第四:低龄娃出现不当行为,千万不要说“不可以”,要用正向的词汇来引导。
有本绘本叫《大卫,不可以》,里面讲了很多大人不同意小朋友做的事情。可是,有些家长给娃看了以后,发现娃更“调皮”了。为什么呢?
因为,低龄的娃,很难理解否定的概念,你跟他说不可以,反倒会强化他的这种行为。
比如你说“宝宝不可以大吼大叫”,他只吸收了“大吼大叫”,于是吼叫得更厉害了。面对这种情况,你应该说“宝宝,我们可以轻轻地讲话”,然后他的声音才会慢慢变小。
如果宝宝很重地打你,你说“宝宝你不要这么重地打妈妈”,他也是不理解的。你应该说“宝宝,你可以轻轻地摸妈妈”,然后给他做示范,怎么轻轻地摸。
第五:家长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不能言而无信。
我不只一次看到过这种情况:大人没有说到做到,言行不一。
比如娃在玩IPAD,家长说再过5分钟就要收起来了。可是五分钟之后,娃不同意收起来,家长随便说娃几句,然后就不管了。
权威丧失就是这么来的额~~~你说你能怪谁啊?
还有些家长,会去跟娃抢IPAD或者电视遥控,要么笑嘻嘻地要娃拿回来,要么一再口头上的威胁,各种指责,偏偏就是没有实际行动。
怎么做才对? 冷静地站在孩子旁边,叫他拿过来,表情要严肃,不要说废话,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用气势让娃就范,这样就足够了。
如果你气势不够,那根据建立权威感的基础,把自己的心理根基打好。
总的来说,建立自己对娃的权威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它会让娃的个人成长,和你们的亲子关系有长期的益处。另外,在根本上,这也是你人生中第二次人格建设的大好机会!这件事,值得你去用心做。
最理想的状态是到了娃初高中阶段,可以和你在外在行为上像朋友一样讨论、交流,但心底里对你像师长一样尊敬崇拜,做决定时是来征求你的意见,而不是想办法绕开你的干涉。这样,你算是成功地做到了一个牛掰的领导。
小罗是一位北漂青年,高中没毕业的他,心中有个歌手梦。
他的吉他弹得还可以,写过几首听来听去没什么特色的歌。在老家,他有个女朋友茄子,他女朋友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就是喜欢小罗,也喜欢小罗的音乐。
“你喜欢什么?”小罗问茄子。
茄子回答不上来,只说:“只要是你的我都喜欢。”
小罗不甘心,他觉得这个茄子不懂音乐,更不可能懂他。
茄子对小罗是真心喜欢,但有时也真心受不了他。在她眼中,小罗总是无缘无故生气,生起气来总要大吼、大叫。叫的不够了,还得砸点东西。
每次小罗生气,茄子都会很害怕,也很难过。
小罗生气的时候,骂人很难听,最常被骂的就是茄子,接下来就是他口中「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的父母。
他恨死父母了,把他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没有钱或任何象样的东西能留给他,有的只是看不见未来的玉米田。
在北京,小罗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友阿枣。
阿枣是个北京人,头发染得五颜六色,逃课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多。
她在酒吧认识的小罗。
那时,小罗组了一个自己的乐队,生活谈不上有闲,但至少慢慢建立了小小的粉丝圈,也有点余钱可以存着买好点的乐器。
每次吃饭、出游,都是小罗掏钱。
其实他每次出钱,心里都不甘愿,因为陪阿枣吃吃喝喝的花销,扣掉房租,等于每个月零存款。
不甘愿,实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压抑。
他想,阿枣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却从来没有体谅他的意思。
矛盾的是,小罗也不愿意让阿枣出钱。在小罗的观念里,这是他该做的。
并且阿枣是个北京人,家里有房有车,本就跟小罗不是处在同个奋斗阶段。
加上从小到大,阿枣本来也就不要特别花心思在赚钱上,父母、男朋友什么的,多得是人帮他负担生活开支。
交往一年后,小罗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常常生一整天的气,又想骂人、砸东西。
好几次他都想把吉他给砸了,这是他最亲近的工具,却也是他发脾气的时候,最想毁掉的东西。
每个人内心的“第三世界”
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的情绪也遵守某种“能量守恒定律”。它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排遣,就会在心中流窜。
并不会因为我们一时半刻忍住脾气,这股或哀怨、或悲伤、或愤怒等负面情绪,就会没来由的消逝。
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在《游戏与现实》(Playingand Reality)一书中阐释:
每个个体在认识这个外在世界,以及世界中的所有客观事物,在“幻觉”与“现实”之间,有一个“第三地带”。
这个第三地带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倾向“幻觉”走向接纳“现实”,很重要的缓冲地带。
有些人在缓冲地带的适应时间太短,就会导致一下子幻想破裂,对现实绝望。
有些人在缓冲地带停留在久,很可能就无法随着年纪增长、社会化的要求渐增,得到对于现实的充分理解与认识,进而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
譬如孩子对世界,原先充满“我是全能的”的幻觉,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自己的一部分,都受自己的意志控制。
而逐渐地,我们理解什么是现实,好知道如何在现实中相处。
所以有天当我们哭泣,也不会有人给我们送上吃的,我们知道自己找吃的。
然后,我们逐渐的不再用“哭泣”去作为索求的方式。
我们开始在社会中,发展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觅食方式,好比各种对应我们个性与专长的工作。
毁掉最在乎的东西,仿佛在自杀
宣泄不了的情绪,停留在我们内心的第三地带。第三地带十分宽广,并非意识能全然领略与控制。
无意识中潜藏的自卑、愤怒与各种负面情绪,有时会不经意的渗透出来。
譬如以小罗为例,每次花钱都会引发他对阿枣的愤怒、生存的恐惧,以及说不出口的那些话,诸如:
“我们不能各付各的吗?”
“操!一直存不了钱,以后日怎么过?我可不像你家里有房啊!”
……
然后,小罗对阿枣就会越来越不耐烦。
因为每次见面就要做他不想做的事,花他不想花的钱。
所以还没有到花钱的时候,他已经压抑不了“幻觉”中可能发生的花钱场景,提前带出愤怒。
还没约会,他就开始忍耐,忍耐不要生气。
约会后,他的负面情绪随着事件到来而达到顶点。
他已经压抑不了内心的情绪,阿枣也察觉到他的不爽,可是小罗不承认自己生气,还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然后在约会以外的时间,小罗爆发,第三地带中那些负面情绪的洪水奔腾而出。
对他来说,现实太残酷。
或者换个角度说,小罗的“第三世界”不足以作为现实与幻想破灭的缓冲。
这也说明:为什么当一个人生气,第一个想毁掉的是自己最亲近的东西。撕毁自己画作的画家、或者像小罗一样砸毁自己乐器的音乐人。
因为当我们毁掉我们最在乎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带有最大幻觉的东西,“想要成名”、“想要成功”的画作或乐器,彷佛在自杀。
自杀取消了我们存在的一切可能,进而使我们有一种解脱的幻觉。
“我不再是那个贫穷的音乐家了!”
“我不再是那个没有才华的画家了!”
当我们不再是那个“连自己都失望的自己”,彷佛内心得以轻松。
但这其实正是一种“幻觉”与“现实”强力碰撞的结果。
我们的第三世界,非但不是连接“幻觉”与“现实”的桥梁,也不是两者的缓冲地带。
反倒成为牵引彼此碰撞的黑洞。
电影《夜行动物》:什么是成熟?
我想起另一个例子。
去年有部电影叫《夜行动物》(Nocturnal Animals),讲述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和白富美相恋、结婚。
结婚前,白富美的妈妈告诉女儿不要嫁给这个生活条件差的男人。
白富美不听,嫁给作家。
过两年,她后悔了,最后和门当户对的男人外遇,甚至打掉作家的孩子,之后两人离婚。
离婚十九年后,白富美收到前夫寄来的小说稿子,一本叫《夜行动物》的小说。
小说讲的是:一家三口出行,遭遇暴徒。男主角为了被奸杀的妻女报仇,最后自己跟歹徒同归于尽的故事。
当白富美阅读这本小说,她感受到了当年自己在作家身上造成的创伤:她外遇、堕胎,就像小说中被死亡的妻子和孩子。
《夜行动物》中的作家,就像开头故事中的小罗。
他懦弱,但他没有能力去抵挡自己的懦弱。他的内心太弱小了,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养分。就像许多早早出社会的孩子,过早迎接太多的现实。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Freud)在《一个幻觉的未来》(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中,谈到一个人的成熟度,就是这个人「接纳未来,将幻觉转化为生存动力」的能力。
成熟的人同样有理想,但他们不会把“理想”和“现实”拉得很开,而是能让“现实”和“理想”接轨。
所以当现实受挫,成熟的人在现实中找方法,而不是将现实的挫折视为理想的破灭。
因为实现理想,不能靠幻觉。而得靠现实中的具体行动。
砸毁乐器的小罗,砸毁的行动不是实现理想的行动,而是理想破灭的宣泄。
换个角度来说,对现实失望,并且对现实无计可施,就只好拿“理想”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少不到无计可施的东西,作为发泄的对象。
回过头来,“假装甘愿”若是造成后续强大的悲愤等负面情绪,从弗洛伊德与温尼科特的理论来说,或许是一个不成熟的个体,拿现实受挫,却又无处发泄的情绪,发泄在幻想出来的对象上。
那可能是小罗的吉他,或是任何一个人身边的一个碗、一个杯子,或是打在某个人身上的一拳一脚。
仇恨的幻觉比温柔乡还可怕
现实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课题跟“甘愿”有关:
一个是面对失去,
一个是面对自卑。
隐忍不甘愿的情绪,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还会形成一种丑陋的复仇想象。
譬如有的男人因为自己经济实力不行被抛弃。
首先,很可能被抛弃的理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因为自卑、脆弱,导致脾气失控,进而引发分手。
进而,他可能会陷入自己哪天功成名就,抛弃自己的女人将如何如何后悔的想象。
若能真的依靠“仇恨”去奋斗,或许还能在成就感中找到生命的出路。
最怕的就是沉溺在复仇的想象,却没有生活中任何的推进。有的只是更多的酒精,导致压抑而产生的更多愤怒。
情绪需要出路,那个出路是“第三世界”的出路。
然而,把情绪埋藏在“第三世界”,存在一个可怕的风险。
当“第三世界”不完全被意识所觉察,这意味着:何时我们的情绪会堆满这个黑暗的地带,蔓延出来成为伤人伤己的暴力,我们并不清楚。
这使我们化身为一个社会上的不定时炸弹。
连结弗洛伊德与温尼科特的理论,所谓的成熟,就是使幻觉与现实达到个体的内在和谐。
而这个内在和谐包括:我们学会面对失去,并学会和自卑共处。
前者后来成为存在主义学派的重要课题,譬如谈死亡;
后者则顺着阿德勒(Adler)的阐发,开展出一系列接纳脆弱与不完美的学说。
作者|高浩容,哲学、教育双博士生,台湾哲学谘商学会监事,著有《心灵驯兽师》等十多部出版品。现居上海,专职咨询与写作。公众号“After之后”,一个除了真相、真理与真性情,毫无其他格调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