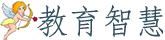七
等我登上新郑的城楼,我终于亲眼看见了人世间最残酷的杀戮,这是我在以往的三十九年的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我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耳闻过许多战争的故事,但从未目睹过。这回可真算是开了眼界。不过让我惊异的是大叔段的非凡表现,我本意是准备看他如何在我的甲士的包围下,绝望地力竭而毙的。我都准备好了美酒,等他的首级一献上,就开怀畅饮。乐工们也早已在堂上堂下各就各位,等我一声令下,就奏起雄壮雍雅的笙歌。我这会目光正疲于奔命地随着段的战车跑来跑去,有好几回,我都看见段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的铠甲上已有多处的殷红,头盔也已不翼而飞,往日的勇武劲健消失如梦。我甚至微微叹了口气,对段的落魄有点惋惜。不管我多么憎恨他,都没法否认,在某些方面,他的确是人中之龙凤。但是转瞬间我胸臆间又充盈了快意,我能以自己的心灵揣想他的悲苦。我想他这时一定有无与伦比的绝望哀恸,他也许在想,何必要听从慈母姜氏的安排呢,老老实实当一个京城大叔不是很好的么?可是,他也应该迅疾会清醒,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吃。他的优雅的贵族生活,将随着他的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我正在思绪联翩,而且我也看到,在这思绪联翩的过程中,大叔段一刻不停地展示着他的可怕武力。他的长戈雷霆般舞动,我的甲士们纷纷倒下,和他同一辆战车中的弓箭手早已仆倒在车耳上,背上插着两枝长矢。他的御者也浑身是血,正疯狂策动马车,意欲远远逃离这阴惨的郑父之丘,沿着洧河,向新郑的东南方向奔去。这天也的确没有阳光,和风扑面,简直让在城楼上的我心旷神怡,远处,碧绿莹澈的洧河上波光粼粼,河边绿树荡漾在五月的惠风下,树下还开满了野花,满眼是黄的和白的。在这样的自然美景之中,我却来欣赏这样暴戾的人文风景,真是充满了滑稽。我的眼光又盯着段的战车了,他的马车真快,那驷马大概都是精心挑选的罢。转眼间,战车已冲出了我方战车的两翼。我一拳砸在城堞上,简直骂出了声。这时我看见我的爱将祭仲也冲出战群,紧随段的战车,他车右的甲士已经不停地向段发射箭矢,可是相隔渐远,简矢往往是未及段的数十尺的距离,就不甘心地落下。我看见段突然把他的长戈插在车上,一弯腰,将车中弓箭手的尸体推下,拣起他的弓弩,引满弓,向祭仲发了一箭。祭仲嘴巴张得老大,似乎惨叫了一声,捂住手臂。接着,他的战车右轮似乎碰到了什么,向左一歪,翻倒在洧河的河岸上。
这场新郑城下的战斗着实可笑,我感到简直受了侮辱。一个疲惫不堪的反贼,竟然挑战到了我的国都门口,我以数倍于他的良将劲卒,竟然也让他全身而退。现在我都没兴趣发怒了。我在想,段会跑到哪里去?如果他真想逃跑,应该在京邑溃败之后,立刻向北逃奔,北边有卫国、宋国、晋国等许多的诸侯,而走南方,要经历大部分郑国国土,这无疑充满着危险。这让我简直要对他发出赞叹了。他不是疯子就是另有打算,难道他留在国内还另有所图吗?而出逃,或许可以借助他国甲士,卷土重来呢。我这时想起,前日卫国的使者已经来到新郑,向我转告了卫君的意思,说段的儿子,我的侄子公孙滑已经投奔他们,并且得到了卫国上下的一致同情。希望我网开一面,能够恢复段京城大叔的地位,兄弟之间不要斩尽杀绝,否则就是违背大周的宗法伦理,不利于天下的安定。
我只是冷笑了一声,竟然跟我讲什么宗法伦理。如果大叔和姜氏知道什么宗法伦理,我又何必走到这一步。如果姜氏知道伦理,她就该明白,作为郑国公室的大宗,她的长子寤生才是当之无愧的代表,她应该把更多的爱倾注在寤生身上,她应该知道,她的荣宠因为有了寤生才能磐石不移,一个没有依托的女人,她的命运,除了回到她戎气十足的故国,应该没有什么好想。她不能做到这些倒也罢了,可是她竟妄想夺宗,那就是太可笑了。
这时候,我隐约明白了段的意图。第三天,鄢邑的使者已经送来文书,段的残卒已经攻取鄢邑,并四处收兵,修筑城池,派遣使者北上,准备和卫国联合,再次向新郑进攻。
提起鄢邑,我实在有老大的不快。那对我来说一直是座不祥的城邑,我的姐姐死在那里,我的父亲武公,据我猜测,他死前的魂魄一直在那里逗留。虽然巫师们不很赞同我的猜测,可是我执意这样认为。我至今认为,也许我父亲武公临死之前有了良心发现,大概觉得人生对城邑和财富的追逐,也不过如此罢。而为此把心爱的女儿当作权量,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又或许他临死前魂魄离散,冥冥之中已经看到了我姐姐哀伤幽怨的脸庞在他奄奄一息的躯体前游回。她是来问我父亲了,是什么能产生那么大的诱惑,竟促使他残忍地放弃自己的血肉亲情。其实,现在我可以代我父亲回答,是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欲,促使他这么做的。如果你还活在今天,你将能看到,你的母亲姜氏和你的弟弟段,不也是这样无耻而贪婪,一意要置你哥哥于死地的么?
我仍有一股亲征的冲动。我想凭借这个追击段的时机,去重游鄢邑。我大概有十年没去那里了。十年前,我修缮了一下鄢邑的城门,在城门下,我低徊不已,似乎能看见姐姐被吊在城门下的惊恐和哀婉。生在一个富贵人家,竟然要这样莫名其妙地惨死。我驻足其间,不禁全身生发出丝丝的寒意。
顺着洧河,我的军队在凌晨登岸,将鄢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
八
但是在鄢邑的厮杀中我没见到段的影子。我的军队很快进了城,后来我才知道,当段知道我亲征鄢邑的第二天,就已经北逃。他历尽艰难,越过黄河,逃到了共国。
我觉得他很可笑,共国也可以算得一个安身立命的选择么?那样小的一个国家,其实我早就想一举将他吞灭了,只是碍于晋国的警告,才一直犹豫不决。对晋国,我确实不敢得罪,它的疆域和实力比我强大得多。但是,关键时候,我也不会手软的。我马上向共国派去了使者,事情已经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共国国君很器重段,也封他为大夫,享受在郑国同样的待遇,他大概觉得收留一个郑国的叛贼,可以起到牵制作用,从而让自己得以苟延残喘罢。何况,段在诸侯间是那样的赫赫有名。
可是他们都低估了我的决心。我也知道,只有趁此机会奋力一击,否则以后很难有机会再杀死段。现在杀死他,可以看成是他反叛时间的延续,错过这一时机,舆论将会倒向他了。时间最容易洗刷一个人的罪恶,与时俱进的罪犯总是容易得到人的同情。对于罪恶,我的感觉也未尝不是如此。如果姜氏和段当初能给我一个喘息之机,我的仇恨怎么可能如此经久靡释呢?
我最终击破了整个的共国,我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这之前我派了许多的使者,和共国交涉,可他们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转而请求晋国的支持。晋国置之不理。我愤怒了,七月,我的军队在淇水之上击溃了卫、共两国的联军。接着,我便得到了大叔段的首级。
他的脑袋盛敛在一个柏木的盒子里,面目很端详。我盯着他,不禁泪如雨下。当然,我不是悲伤,但是我为此记起了年轻时的许多事。段毕竟只小我三岁,在能分辨出各自的身份地位之前,我们的友谊也曾经如寻常人家的兄弟一般的融洽,我们和我们的姐姐也常常在一起嬉闹的。他的额头有一个疤痕,那是我用棋局掷伤的,那是我看不惯母亲对他的热情,而迁怒于他的产物。现在那疤痕宛然如新,而这个人却身首分离,再也不会有欢乐和悲伤了。
我不是一个冷血者,所以能对着他的头颅缅怀少年的时光,那样久。昔日的阳光似乎已经悄悄移进大殿,照耀在我的身上,和他的头上。阳光是发黄的,承载了几十年的岁月,我的记忆也是泛着那样陈旧的黄色。
蓦地我回过神来,我难道忘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么?现在我要带着这颗倔强的脑袋去见他的慈母了。想到这里,我嘴角荡漾着笑容。
北宫还是那么阴冷,母亲被冷锢在这里已经一个月。我和段的战争持续了一个月,我没有时间来理她。也许今天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当时我叫祭仲去宣告禁锢她,我曾说不再与她相见了。但接着我改变了主意,我想等到亲自送段的首级来这里的一刻,仔细欣赏她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等了三十九年,不就是等这一天吗?
大概母亲也知道了一些消息了。我见到她时,她脸色已经很憔悴,似乎久已不曾好好饮食。不过她并不愿正眼瞧我。这符合她的身份地位。在我面前积渐的威权也使她要保留一定的矜持,她怎么甘心在一个她一向可以颐指气使的人面前低声下气呢?
本来见到她时我还有一些踌躇,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仁慈的人,但也不忍亲眼见到别人落魄的样子,特别是老年人,他们的蓬头垢面,他们的可怜会被他们满脸的寿斑和皱纹夸大,让人简直不能想象,他们也是从白嫩光滑的少年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母亲也是如此。就我挑剔的目光来说,她以前也曾是一个美人。几十年来,岁月的风霜虽然侵蚀着她,可是这一个月来的变化也是有点让我不能接受的。一刹那间,我都几乎有点可怜她了。她对段的溺爱我都准备一股脑的接受,我甚至有点羞愧,怎么能带着段的头颅来见她?我真有点退缩了。说实在的,虽然对于段,我有杀之而后快的意图,可是对她,我得承认,我的恨意并不多。多年来,我只想让她明白一个道理,她对段的偏心是过分的和有悖情理的。我的要求真的不多。
但这时,当看到她眼中的仇恨和冷漠,我隐隐愤怒了。我脑中几乎是不假思索,发出了这么一个命令:
“把礼物献上来。”
当即,段的头颅就傲岸地躺在她的面前。虽然我已有准备,但是我仍然没想到她的反应是那么强烈,强烈得我已经用笔墨无法形容。但是我可以说说我的内心感受,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一个无形的铁钩揪住了一般,接着,五脏六腑在肚子里翻腾。我可能是受了惊吓,也可能是因为愤慨促使我生理反应如此。我一向以为,一旦看到母亲悲痛欲绝的样子,我会有凌云般的快意。这可是我多年盼望的啊!可是当我听到嘶声的一声长哭,我心头却奇怪的只有痛。平静地叙述也是可能的,因为要我描绘她的内心,无疑我做不到。我只看见她枯瘦的手指在筵席上狂抓,泪水伴着哭嚎涔涔而下。她的哭声偶尔会中断一下,以堵塞的呜咽声来填补。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想我该离开,但是腿却迈不动。
我必得做点什么以镇静自己的心神,于是我假意地怒吼,我知道自己的愤怒早已荡然无存,我吼道:“你哭什么?如果不是你的纵容,段怎么可能落得如此下场。如果不是你凶蛮的野心,危及到郑国公室的安危,乃至激起了众怒,我怎么发兵去讨伐他。即使我再听从你的意思,对他的贪欲置之不理,也没这个能耐。整个宗族都将反对我,我身为国君,怎么能做宗族的表率。是你这个母亲的无原则的溺爱毁了段,何况你竟想暗中开启城门,为他的袭击新郑做准备。你一步步将他引进了死亡,还有什么脸面悲伤?”
母亲的哀戚并没有停止,她哭声依旧。这让我的愤怒逐渐上升,于是我把随身带的简册扔向她,同时宣布道:
“也许我们本不该做母子,这是上天的错误。这样也好,洧水的清澈,我不能和你共享。你马上迁居城颖,也许颍水之波能洗净你灵魂的罪恶。从今天起,我们母子恩断义绝,不到黄泉,誓不再见。如有违背此誓言,明神在上作证,让我宗族覆灭,死无葬身之地。”
九
母亲终于离开了她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新郑,带着少数几个仆从去了颍水之岸的小城——城颍,它另有个别名叫临颍。那是郑国的边邑。她走的那天,我强忍着没去目送她离别的身影。有好几次,我都望着新郑的南面角楼发呆,我有冲上去俯视母亲车仗的冲动。我知道,祭仲正在给她祖道饯别,虽然她对不起我,对不起郑国公室,但我并不表现得很残忍。相反,我对她的离去有些怅惘,这时我表现得象个很正常的人,我有正常的渴慕亲情的需要。我知道,有些时候自己是不大正常的。
但是,我为自己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我不能去看她哪怕只是一个背影。我已经发下了毒誓,不到黄泉,绝不相见。我知道,天上的明神对我们誓言无时无刻不在监听。如果违背,我无疑会落到比段还悲惨的下场。不但会失去我的生命,整个宗族都可能因为莫名的原因而夷灭。这样的事情,我只是道听途说过很多次,但我对之深信不疑。重大的事情,我不敢拿来开玩笑。况且我知道自己,我是个敏感的人,即使上天并不准备惩罚我,我自己也会在终日的自责中忧惧而死。我怕死,是的。难道我处心积虑的追杀段,不是因为自己的怕死么?难道我在母亲面前那样的愤怒,不是因为怕死带来的过激反应么?我长期遭受的漠视的亲情固然是我嫉妒、愤怒的一个方面,而深藏背后的原因无疑仍然是怯弱。这个,我突然想得很清楚。
母亲走后,我觉得宫廷里缺了点什么。我会在夜晚起来,望着北宫的方向沉思。那里以前也曾是灯火楼台,特别是在段回新郑的时候,北宫的灯火几乎是终夜不灭的。虽然我也会去随喜饮宴助兴一番,但不会呆太长时间。剩下的时间全是他们母子的。虽然那让我嫉恨,可是,比起现在黑灯瞎火的荒凉,那些嫉恨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我怕荒凉,比任何事情都怕。昔日的欢乐,只剩下如今我孤零零的一个。这让我有点心如刀绞。我痛苦地想,为什么母亲,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现在我明白了,我能忍受你对段的溺爱,但我不能忍受,你想把这份溺爱建立在我生命的基础上。你不该毁灭一个来成全另外一个,你不该对一个锦上添花,而试图夺取另一个怀中仅有的炭火。你真是太偏执了。就因为这,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原谅你,我能从你这里找到什么母子之情呢?
在母亲身边,我没有安插任何人,因为既然我发下了毒誓,今生不会再和她见面,也就丧失了想了解她的欲望。在我心里,了解她也意味着一种背盟。虽然,我时时有些后悔,我还是想知道她的。倘若我只是在杀死段之后,将母亲驱逐,那么我一意要取得段的首级的意义何在呢?杀死段是为了让母亲悲痛,而我能从旁欣赏她悲痛给我的快意,我想让她后悔。但是那天在她面前,我的快意没有得到,她也似乎并没有后悔。不过也许她会渐渐后悔呢?只要我能日日了解母亲的内心,我就觉得我前此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把她放逐并不是我符合我潜意识的初衷。
有一天年终,临颍来了一个官员,他是来上计的。每到年终,新郑要比往日热闹许多,因为这是各地官员进京述职的时间。临颍的官员名叫颍考叔。
在一切公务办完之后,颍考叔给我上书,说有一些土特产要献给我。这个我不稀罕,颍水离新郑算得比较远,但是大概还不至于远到有什么珍奇物品的地步。然而我心里一动,他是来自临颍的,母亲现在就居住在他所管辖的城邑里,也许他能带给我一些消息呢。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我对一切含有颍字的地名都有一份敏感。我也不愿意承认,我已经从心底里原谅母亲。只是我想承认,我对于荒凉的害怕大概要甚于对死亡的害怕。当然,这个原谅经不起考验,荒凉是什么东西呢?荒凉不是来源于死亡么?我又一次远远望着北宫,那阴森的大殿曾承载了往日的多少欢笑,我的父亲曾不计其数地在这里和宗族宴饮,往日座上的白头翁已经大多入土,稚嫩的少年都已走过中年。尤其是我繁盛的一家,现在能接近它的只剩得我一个。宴饮的主人墓木已拱,英俊的大叔段也魂断不归,衰老的母亲在远方茕茕愁苦。我于是想,倘若在这场冲突中死的是我,留下的是段和母亲,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我一点呢?我所害怕的荒凉,到底无一不是和死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如此,我的想法都是很矛盾的了。
然而我仍想见见颍考叔,既然我的心底放不下母亲,那么就干脆问问她的情况,这大概终究不算是违背誓言罢。 颍考叔是个看上去很健壮的人,精力充沛。我们君臣客套了一番,他没有提起我的母亲,好象他辖下的那个人,那个从前的国母从来未曾存在。我也强忍住不提。不过在飨宴他的时候,他突然把一些肉放在另外的簋里。我奇怪地问,怎么?你是嫌寡人的庖人技艺差么?抑或你对肉食不感兴趣?
这个健硕的男人腼腆地笑了,他说:“主君见笑了,臣一个下级的官员,能得到主君的宴请,真是无任荣幸。岂但是臣本人,臣整个家族的祖先都将享受这无上的荣耀。臣的母亲从小教导臣要恪尽职守,为君王分忧。现在臣能和主君坐在一起,不正好证明了臣没有辜负母亲的一贯教诲吗?刚才臣突然想,如果能把主公的食物带一点回去,给臣的母亲尝尝,她该是有何等的欢喜啊。臣所能孝敬母亲的都已经孝敬了,惟有君主之赐,恐怕她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而如果竟能实现,臣在宗族间该多么有脸面,这样不是可以激励主君所有的臣子,更加鞠躬尽瘁为主君效力吗?”
天,这个虚伪的人,他说的什么?从新郑带上我的食物去临颍,他是不是疯了。不过,他说的难道没道理吗?至少极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能想象她的母亲在接到我的礼品时,该是何等的欢喜,他在宗族间也会更有声名。可是,他的话肯定不仅于此,而是有着更深的含义,于是我的身子往前一欠,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有母亲可以孝敬,可是寡人没有。寡人很艳羡,寡人家族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现在你给寡人想个办法?怎样才能让寡人的母亲回来。你不是想影射寡人吗?你想说的是,寡人有你这么一个孝顺的臣子,而他的君主却对自己的母亲残酷无情,这将在诸侯间传为笑柄。当然,寡人宁愿往善良处想。你是不想让我们郑国公室背上冷酷的名声,而要上下一致,以孝立国。那么,你就赶快给寡人想一个办法。寡人曾向母亲发过恶毒的誓言,如果不到黄泉,绝不相见。那样的日期永不可乞盼,意味着公羊能生出小羊。如果你能够想出办法,那你就不算有头无尾了。否则你说了这些有什么用呢?你不会是专程来讥讽寡人的吧?”
颍考叔的脸色有些惊慌,他赶忙声辩,不过也不再卖关子了:“主君,”他诚恳地说道,“臣知道主君的誓言。但是如果主君肯挖一条能看见泉水的隧道,那不就应了主君发的毒誓吗?黄土之泉既已见到,而隧道也不正象下葬时的羡道吗?不管是实在或者象征的意义,主君都给了它满足,再加上主君赤诚的孝心,上天有什么理由不原谅主君呢?恐怕反而会为主君的赤诚感动,从而降给郑国无边的福禳的。”
我望着颍考叔,他真会动脑筋。我有点惊叹了,不过我迅即明白这是最好的办法。既然我想在诸侯间有好的声誉,既然我想重新看到母亲,我就得采用这一办法。我知道,外面的流言已经很沸沸扬扬了。谁都在宣传,郑国的国君是一个为了利益,非但容不下手足兄弟,甚至连亲生母亲也能毫不犹豫地放逐的人。别国的使者来觐见我时,涉及到宗庙亲情的话题,我似乎都能毫不困难地看到他们嘴角的诮让。这些场景屡次让我坐立不安,更为重要的是,我心底里知道,只有得到母亲的承认,才能义正词严地宣告,我在这场冲突中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否则我又比我的祖父桓公、父亲武公高明到哪里去了?既然大家最后都落下残酷和冷血的声名,我以前对段的容忍,又意义何在呢?
我还得说,我对母亲仍怀有希冀,我希望她能在失去段之后,继而接受我,给予我亲情。毕竟,我是她剩下的唯一的亲生儿子。相反,对我来说,能实施对母亲的孝敬也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既然宗周的礼乐一切都以宗族亲密为基础,那么顺应这故俗就是无上幸福的。孝敬在这时已不仅仅是我个人得到满足的事,更是让别人从我的行为中得到满足的事。我知道,我能从母子和睦亲热中得到满足和快乐,很多的人更能从我们的母子和睦亲热中得到。如果不是这样,我身后的宗庙威严也都丧失存在的理由了。
我决定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我还有点忧虑,不知道母亲的意见是怎样的。虽然,我希望尽力恢复母子关系,但是她怎么想?也许她因为爱子的丧生而依然在心里对我保持恶毒的诅咒呢。
颍考叔笑着说:“主君不必忧虑,臣听说郑姜夫人现在也已经很后悔,她常常在悔恨自己以前对大叔段的溺爱呢。她的侍女说,她曾经自责,如果当日认识到,不能以个人的好恶而废弃宗庙的责任,那么一家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主君如果能主动示好,臣想郑姜夫人定是求之不得。主君和母亲的重新和睦,将是郑国的鸿福,我郑国在诸侯间也就更有声誉了。臣知道主公素有大志,以和辑诸侯,藩卫成周为己任。所谓欲治一国者,先齐其家。主君自身行止白璧无瑕,将不会给诸侯以任何口实。加上主君又身兼天子朝廷的卿士,以自身之光洁,依怙天子之威,出纳王命,诸侯怎么能不仰视呢?我郑国乃新造之国,而在中原的地位将更稳固了。”
他真是能言善辩,我有点喜欢他了。于是我决定把一切事宜都委托他,不过行止一定要秘密。等到地宫和黄泉隧道修治完工,我将立即去临颍。虽然我有点心烦意乱,对这样的做法不知所措,也不能清楚考虑将出现的意外情况。但是我不是没有信心,也许会有些尴尬吧。但是宗室的礼节,细思起来,尴尬的本就不少,我想,只消把这一切当成一项新排练的礼仪活动去看,也就释然了。然而,我的确没想到,有那样意外的事情发生。
十
走在通往幽暗地宫的幽暗的隧道里,我有一些怪异的感觉。夯土的台阶很坚实,体现出颍考叔良好的办事能力。但每一步都让我脚步发飘,我知道母亲正从那一头的羡道走过来,此刻,她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在不久前的斗争中,我是光荣的胜利者。我知道,自己本该以大度的姿态去接见母亲。她虽然是母亲,是前此的一国小君,可是她没有遵从宗族的礼法,她犯了大错,而为礼法所不容。即使我的姿态再高傲点,那么从原则上说,我并没有错。无知的小民,他们爱传唱什么就去传唱什么吧。我知道,此间的童谣正在这样羞辱我,这在新郑,我是没有听到的:
戋戋之布,尚可缝兮。
寥寥之黍,尚可舂兮。
兄弟二人,不相容兮。
戋戋之丝,尚可就兮。
寥寥之粟,尚可捣兮。
母子二人,不相好兮。
他们的传唱虽然不会被礼法认可,但是,乍然一听到这样对国君的侮蔑,总不是件痛快的事。我并不想武力镇压,我知道,那样不管用,反而更显出自己的心虚。而且,我为什么这么在乎百姓呢?我现在正在做的,与其说是为了好名声,毋宁说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我不能漠视自己这样一种和母亲的关系,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我本来就是个脆弱的人。
我早就不想以高傲的姿态去对待母亲,但是这一刻,我仍旧有点忐忑不安,已经几年没有见到她了,她大概比以前更加衰老。她还会在心里保持对我的仇恨吧?也许我不该杀死段,当初他逃到共国,我让一步,放过他就是了。但是当时,冲天的仇恨蒙蔽了我的双眼,我只想得到他的首级,我只想提着他的首级向母亲示威,隔着帷帐扔向她,对,一定要隔着帷帐,这样才有巨大的惊悚效果。我想把头颅扔进去的同时,爽朗地大笑:“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宠爱的反贼段。他斗不过我,我轻易地斩下了他的头颅。你可知道,你选错了人,你为什么不长一双慧眼,将你那无私的爱转移到你更有出息的大子身上?现在你该为自己的举动后悔了吧。”
但是母亲没有后悔,她只有悲嚎,那种无视死生的悲嚎。我大大地打错了算盘。悲嚎,无视生死,我不由得战抖了一下。
槨室里灯火通明,甲士们举着火把,分列两旁。我又看见母亲了,她果真比以前更加憔悴。父亲在时,光阴好像对她的脸无所作为,几十年来,她的脸都是光滑的,这未必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近视她的原因。现在她头发斑白,皱纹满布,昔日养尊处优的痕迹已不复存在。惟有眼睛中不经意透出一丝威严,尚依稀可见当初郑姜夫人的影子。我心里有些痛,看到老年人的可怜老态,不由自主萌生的痛和恻隐。我动感情地叫了一声:“母亲!”
母亲也朝我疾步奔了过来。她叫了一声:“寤生。”然后抱住我远比她高大的身躯,接着我突然感到腹部一痛,钝痛。我脸色煞白,两臂一张,推开她。她尖叫着跌倒在地,惨笑了一声:“我早该想到,寤生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没等我做出什么反应,她已经用手中的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槨室里发出一阵喧哗声,显然大家都被这样奇怪的场景惊呆了。我抚摸着刚才钝痛的腹部,今晨,我鬼使神差地穿了一袭重甲。然而,倘若不是如此,那把插进母亲胸口的刀已经刺进我的腹部了。
天,我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阴森森地盯着颍考叔。他早已张大了失神的眼睛,跪倒在地上。我愤怒地抢过身旁甲士的长戈,想朝着他背上狠狠砍进去。但是,仓惶之间,我的戈止住了,我颁布了关于我们家族内部事件处理的最后一个命令,也许这个命令不是那么完美,但确实,在这种场合下,还算是完美的。我踢了颍考叔一脚,说:
“立即起驾,回新郑,向郑国境内三十六个城邑和其他同盟诸侯宣布,郑国国君和其母亲郑姜夫人和好如初。黄泉誓盟之所,将修筑新城,成为郑国重要城邑,立宗庙,世世祭祀,以劝国人。”
在颖考叔的带领下,羡道内响起了欢呼:“主君和他母亲和好如初啦,万岁!”我回味着“如初”两个字,感觉泪水生涩地在心底潜流,叮咚有声。
(选自微信公号:梁惠王的云梦之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