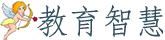四
虽然我知道段的势力潜滋暗长的危害,但我也不是傻瓜,想着去主动翦灭他,这样是很得不偿失的,那可能会带来终身的懊悔。因为我无法消除积蕴心中几十年的愤怒,是我母亲姜氏开启了我的愤怒之门,而她从来没想过补救,这愤怒我非但铲除不了,而且与日俱增,它就象春日宫门阶砌下的芳草,日复一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母亲带给我的屈辱,我所有的欢乐和悠闲就会霎时一扫而光,立刻萌生一种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任凭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是的,我要毁灭他们,但不是杀死他们的全部。我只是想杀死段,那样我母亲将会极为悲伤,这悲伤才是我极意想看到的,那比在我面前展示一万个千姿百态的裸体美女还要快意。看见一个人,一个你本该亲近却忍不住憎恨的人,在丧失了精神寄托后所展现的那种空虚凄凉,无疑有另一种极端非凡的美感。死,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活着。
我已在脑中预想了千般段的悲惨命运,以及我母亲的哀绝,心底就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那是和抱着美女上床截然两样的快感。我会为之泪流满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因为,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才可让母亲刻骨铭心地感觉,她当初的慈爱完全放错了地方。相貌的英俊并非判断成败的依据,有什么比见到别人号天悔恨更欣悦的么?每个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不体验着实可惜。
“主公应该果断地下命令了。”我正在想着,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公子吕轻轻地走到堂上,侧身跪坐在我东面的席子上。我看了他一眼,朝晖斜射入帷帐,他面前的几案一片灿烂,这使我马上产生了莫名的雄心,看来他好像很同情我。虽然我最反感同情,但还是感觉到一阵温暖。公子吕是我的哥哥,不过他是庶子,他的母亲比我的母亲姜氏地位低下,也许不那么高尚的地位,反而能使他对我这样拥护。只是我宁愿认为,他对我的关心是出自真情。我庶出的哥哥吕,和我同产的弟弟段,两者竟然构成这样奇特的反差,我相信我的一切屈辱他都能切身感受到。天!难道我一直过着一种在家族中庶子的地位么?我难道不是郑国响当当的大宗么?
我于是愤懑地说:“你觉得我该下什么决心呢?”
“翦除大叔段,或者改封他邑。”吕说。他的话和祭仲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声音轻轻的,简直怕伤了我,那么轻,那么柔和。
“什么大叔段,是逆贼段。”我终于失态了,愤懑地说,“大这个词是能够随便拿来做任何修饰的么?他只用于增加国家之大宗的荣耀,它只能锦上添花,而绝不允许用来雪中送炭。没有我的宽容,段只是一介匹夫,他那样卑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使用这样一个伟大的词汇。”
“主公,你愤怒也没有用。”吕说,“事实上段早已经以大叔闻名诸侯,他现在已经命令东鄙和北鄙两个城邑服从他指挥了,我们派去的地方官员在那里已经收不上任何租税。主公,你应当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大叔段得了这两个地方,就有更多的资源和我们对抗,民众要仰衣食于他,就不会再听主公的命令了。”
我心底冷笑了一声,段,你也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有足够的势力和我抗衡么?依照京邑的岁入,再加上东西二鄙,也及不上新郑和制邑的一半,你那点岁入能装备几辆兵车?就算是两百辆吧,又能是我的对手?郑国,怎么说也是个能拿得出两千乘兵车的国家,你依旧是以卵击石。再说我在京邑也派遣了很多间谍,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我的股掌。有勇无谋的匹夫,怪不得母亲那样几次三番的乞求,怪不得父亲平时那样听母亲的话,他到底没有立你为太子,因为你确实不配做郑国的国君。
不过我心里仍然丝毫不想主动出击段,那样虽然很容易,但是会降低我作为一个国君的层次。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以狡诈冷血闻名,固然,这是个很优良的品质,但未免太赤裸裸了,连友情和亲情都赤裸裸地当面撕裂,污血就那样随着崩裂的创口溅射而出,这固然也很带来快感,但同时也会弄脏精美的华衮,让人君等同于臧台,丧失伟大贵族该有的风度。祖父和父亲曾一度受到周天子的指责,这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我不愿这样,我只是心急如焚地等待段的主动,如果他主动,我就可以一石数鸟。我既杀死了我的仇人,又能让我的母亲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而且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她的这痛苦还只能藏在内心,根本没有辩驳的机会。同时我在外面也能保持温润如玉的形象,我仍是那个人人称颂的既孝且悌的郑国国君。可怕的人啊,可怕的内心,我简直被自己的阴鸷吓坏了,以至于可能脸上丧失了血色。我的庶兄身躯朝前弯了一弯,很关切地问:“主公,你身体不舒服么?”
我摆了摆手:“没什么。你放心,段是我们的公族子孙,也是优秀的人才,他不会反叛的。倘若会,他就丧失了宗族的合法基础,他得到的土地越多,他栽倒的日子就越快。”
虽然我是这么说,其实我也开始隐隐生出一些忧虑了。如果他这样对我的土地侵渔不已,而又并不来攻打新郑,我到底该不该忍住,不去主动翦灭他。不主动恐怕不行,虽然这有点违背我原来的计划,但是……
我想起了母亲姜氏,我想,这样一件尴尬的事是她促成的,她也应该有责任来完结它。我于是穿过复道,向她住的北宫踱去。
五
也许是我给母亲的暗示起了作用,我派在京地的间谍陆续传来的消息,让我暗暗窃喜。段果然已经沉不住气了,我的母亲姜氏给了他最大胆的安慰。由于我在母亲面前总是极力列举段的种种好处,让母亲也对我稍稍有点亲近的迹象。但我知道,那亲近是拜段的所赐。这算什么,我只有托段的荫庀,才能从他那里分享母爱的一点残汤剩羹么?这种散食我不需要,不足以填饱我三十九岁的空虚的心灵。我即位已经二十二年了,该忍的已经忍受够了,现在已得到时机,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彻底找回补偿。他们也应该把欠我的还我了,在这个问题上,利息都已远远超过本金,我绝不允许有一丝半毫的赊帐。
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段准备在五月朔日夜袭新郑。我望着祭仲、公子吕,面色凝重。虽然我在他们面前不想伪装,但是也不想显出过分狂喜,那是浅薄小人得志的神态。我时时提醒自己,你是郑国的国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饱含风度,迎合礼法。不管,是的,不管这风度和礼法下掩盖的是一摊多么腥气冲天的血水,这也不是我所盼望的。我也想做到不让华美的衮服有一丝的褶皱,也想让那和悦的笙瑟是醇净而不掺杂间音的。在诸般的波澜不惊中,我们的郑国国土日渐广大,我的位置也如那磐石般稳固。但是,这多么难办?
公子吕慷慨地说:“主公,臣请求先发制人,请立即给臣二百辆兵车,臣率领一万五千甲士杀奔京邑,击破反贼,给主公献捷,维护我郑国的安全。”
我缓缓点了点头,有种如泣如诉的快意,如潮水般漫到胸部,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我想自己需要独处来享受这窒息带来的快感。我极力抑制住自己,发布了一道我人生中最迟到的命令:
“子封。”我叫着公子吕的字,“寡人命令你,立即率师杀奔京邑,击破逆贼段,光复我先君武公之旧土。”我转过头:“祭仲,你也立即去搜集姜氏和段来往密信,等京邑击破之时,立即带人进驻北宫,向姜氏宣布寡人的命令,将其流放城颖——并带去寡人的誓言。”
说着,我扔给他数枝竹简,那是我早就写好了的。大概写了十多年,墨色都已变得黯淡,可是我竟然不想重写一遍。虽然为了掩饰起见,我本应该假装是怀着愠怒最近写就的:
“《诗》云:母氏劬劳,而何不能普施慈爱,只流惠于悍弟?寡人独非君之亲子乎?乃险被惨毒。母氏心何忍也?自今之后,君其移驾城颖,保厥余年。不及黄泉,毋相见也!”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面上挤出一种忧伤的神情。天,我真是虚伪到家了,本该是欢喜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在这里装腔作势,真是难过。我有点忍耐不住了,我差点忘记了对贵族礼节的起码理解,想一跃而起,跑到内廷去高声呼啸。我真是忍不住了,于是我抬起一条腿,想要站起来,同时叫他们赶快告退。
祭仲则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满面笑容,谄媚地说:“主公英明,早该如此决断。姜氏如果不这般偏心,宁有今日。《书》不云乎: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主公不要忧伤,乃是姜氏不仁,有违礼制。主公这样的处置,已经算是很仁慈了。”
这个孩子真是乖巧,才二十二岁,已经深得侍君之道,这么善于拍主子的马屁。不过我还是微笑了一下,说:“我累了,你们先告退,下去执行吧。”
六
我至今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公子吕的军队出发时,我为他举行出发仪式,祭祀大路之神,希望他此行顺利。我毕恭毕敬地履行了这个仪式,整个仪式持续了一个时辰之久,这期间我的心脏一直乱跳,惶恐不安,脑海中一直浮现出段执戈袒胸刺虎的英武。我知道段勇力过人,为公子吕的成败与否暗暗祈祷。等到仪式结束,我跪在公子吕中军的大旗下,用力把车毂往前一推,说:“祝大夫此去,顺利击破反贼。阃内之事,寡人主之;阃外之事,全托付给大夫了。寡人日夜等候大夫的捷报。”然后我看着战车碾过草制的雏狗,半晌不语。
虽然计划一直是我早就盘算好的,可是临到头我却如此惶恐。最心烦意乱的是,我很怕自己在某个环节出了疏失,从而一败涂地,那就再也看不到我的母亲姜氏的绝望神情。那种神情虽然还没出现,但已被我在心中臆想过千遍万遍,那简直成了我三十多年来生存的唯一理由了,是我的精神支柱。我马上要收获丰收的果实,却怕收获前夕突如其来的冰雹,将果实打得稀烂。我可不希望,陷入万劫不复的是我自己。
还好,我日夜的筹算没有白费。过了几天,来自京邑的捷报已经频传到新郑,洧水上,冠盖相望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带来类似的喜讯。我在京邑中埋伏的间谍起了作用,当公子吕的大军到达城外的时候,京邑的守御还是很严密的,两军交战了一天,死伤数千,没有一点战果。我确实小觑了段治军打仗的能力了,但是幸好,在政治上他是一个白痴,交战的当天晚上,我的间谍们在京邑的各个里巷散布谣言,说主君的军队已经趁黑击破了京邑的东门,京邑民众应该立即停止反叛,主君已经传下命令,凡是本身不想反叛,只是被大叔段裹胁诖误的,一概不予追究。命令下达之日,如果仍然负隅顽抗,那就只有全部屠戮,不留孑遗了。
这个谣传的确很有效果,民众大部分放下了武器。等到凌晨,公子吕的军队已经进驻京邑的宫廷。我的同产弟弟大叔段率领他余下的徒众向东南方向狂奔,目标可能是新郑。这个狂悖的反贼,难道凭借一点刚刚溃败的乌合之众,他竟敢进攻我所在的国都么?
虽然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却竟然是事实。段真的率军往新郑而来。离新郑不远的郊区,谍报发现了大规模的车队,黄尘蔽天。战旗上大书太叔段的字号。这消息简直让我作呕,反贼段也太不自量力了。我做出了一生中很大胆的一个决定,准备亲自率领中军,去和段对垒。我已经好多年不见段长什么模样了,因为他好多年不曾回新郑,大概在心底他早已不把我当国君了。不过我无所谓,他来觐见我与否根本丝毫不能减轻我对他的憎恨,只能加强我的厌恶。老实说,他的一举一动,饮食、说话甚至走路的样子都让我看了作呕。不过,他的缺席对于母亲姜氏来说相当残忍,也许这正是姜氏想要尽快除掉我,立段为君的原因罢。
我的中军在新郑的郊外停住了脚步。这片平原叫郑父之丘,是祖父命名的,也将是我胜利的阵地吧。我看见段也站在对面的大旗之下,他神情有些疲惫,白皙的脸上夹杂着灰尘和血迹,可能在逃亡中经受了不意的磕碰,不过他仍旧威仪棣棣,眉目间仍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轻蔑之气,那是淫浸三十六年的贵族气息,虽在惶恐奔命之中犹不稍减。这陡然让我的厌恶减轻了许多。心里暗暗赞叹,不愧是我们的公族子孙。他手中横持一枝长丈余的大戈,和当年短衣刺虎的从容之态完全两样,眼眸直盯着我,目光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还是你奸诈狠毒。”段刚才还杀气腾腾的眉宇间露出一丝苍凉,“不过,我只请求你,不要和母亲为难。虽然我承认,她对你的慈爱不够,我攫取了本该和你分享的慈爱。但是,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她毕竟生下了你。”
我开口了:“大叔段别来无恙。”我带着揶揄的口气说。我有这个资本。在我的身后是一支五百乘兵车的队伍,左右两翼形成了向前的弧形,象鸷鸟的两个翅膀,把段那支不足百辆兵车、步卒杂然无章的队伍包裹在其中。只要我一声令下,他和他的这些徒众,马上会像刚出鼎镬的羊肉羹,不需要我的勇士们分泌太多的胃液,立刻就会将之消化得无影无形,次日连排便的感觉都不大会有。
“简直可笑至极,你还有脸面提这个。”我哈哈大笑,“不错,是她生下了我。但是她起初并不想顺顺当当生下我,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就想对我进行谋害。她让我脚先于头来到世间,无疑有着让我窒息而死的阴谋。然而我那时就粉碎了她的阴谋,我还是活下来了。她则采用另一种卑鄙的做法,借口我的逆生对她造成了惊吓,从而赠予我长达三十九年的冷酷,三十九年,我真佩服她的耐心和持之以恒。这期间我对她百依百顺,为了就是她能良心发现,翻然悔悟,从而把给你的关心和爱护匀一点给我,可是我的孝顺和宽容换来的是更无耻卑劣的荼毒。她想夺去我的一切,连父亲给予我的,她也想抢去转赠给你。的确,我早已不期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可是我自己的,她亦没有资格,也永远不会有可能拿到。况且,宗庙神器,本来也不是我个人的,即使我想满足她无耻的贪婪,转赠给你,我自己也绝没这权力,因为先君桓公、武公的魂魄一直在天际注视着我,我只是郑国宗庙的一个守卫者,于国家社稷,我也是一个过客,我有什么资格给你呢?而姜氏,只是一个姜氏之戎的女子,她的血液中永远残留着无法稀释的粗鄙和野蛮。当年就是他们的族人和犬戎一道,弑杀了我们的天子,使我们放弃了号称天下膏腴的宗周,迁徙到黄河以东。她的内心和她宗族的传统一样卑劣,想起这些足以让我天旋地转。这下你该明白了,你们,不是我寤生的敌人,而是整个姬姓家族的敌人。即使我想发出天底下最慈悲的善心,饶你们一条贱命,然而在告祭天地祖宗之时,我又当如何去面对?你们辜负了祖宗的荫庀,做出了这样丧尽天良的恶行。郑国已经没有一寸土地愿意掩藏你们龌龊的尸体,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即使我把你们龌龊的尸体投诸黄河,黄河也会终日呜咽。不是为了你们肮脏的死而呜咽,而是为了不得不承载你们龌龊的尸体,而感到极大的受辱。”
天,我竟然说了这么多。我真佩服我的口才,也真佩服我的耐心和风度。我难道为了证明什么,竟迟迟不肯对眼前的仇人下手么?对,要是换了我的父亲武公,他才不会象我这么多的废话,他早就将他的长剑往前一指,弓箭手已然万箭齐发,战车也早已轰然滚动,身披重甲的车兵早已杀声震天,突入对方的阵地了。不过,也许我得再废话一下,我的确看不起我祖父和父亲的类似做法,他们虽然勇武和残酷,却终究不是上乘境界。真正的上乘境界应当象我追求的那样,谈笑之间,敌人灰飞烟灭。不管在道义上和军事上,敌人都将堕入不齿于诸侯的狗屎堆。据说这种行为叫伪君子,可是伪君子有什么不好,难道比臭名远扬的小人还坏?伪君子至少可以欺骗一撮人。如果好,可以是一大撮;即便差,也至少有那么一小撮。何况,对于大叔和姜氏,我的容忍已算得很多。
大叔果然张口结舌,他一向是这样拙于言辞、长于行动的。隔得不算近,我却仍看见了他涨红的脸和额头上鼓胀的血管,象男人的阳物一样勃怒。我鄙视地看了他最后一眼,拔出长剑,吼了一声:“给我上!击杀太叔段者,金千金,邑万家。进军。”
霎时间,万箭穿空的尖锐叫声不绝于耳,战车的轰隆声、身披重甲的步卒的呼啸声也此起彼伏。车夫把驷马的缰绳往左一提,使我乘坐的战车隆隆回驶,向新郑城内奔去。我准备登上新郑的城楼,在那再安全不过的地方观看这场擒杀逆贼段的战斗。
(选自微信公号:梁惠王的云梦之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