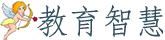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尊重。
你的朋友向你吐露了隐衷,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向人传说。也许你的朋友还向别人吐露了这隐衷,你仍要当作只有你一人知道一样,不可让秘密由你传播出去。
你的朋友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出现。但是,这不能成为理由,认为你因此就有了随时在他面前出现的权利。即使对你最好的朋友,你也没有这个权利。
当你的朋友处在大幸福或大悲痛之中时,你要懂得沉默,不去打扰他,这是一种尊重和教养。
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益,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有自己的行话。有时候,不同的行话说着同一个意思。有时候,同一种行话说着不同的意思。
隔行如隔山,但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头,灵魂之间的鸿沟却是无法逾越的。
我们对同行说行话,对朋友吐心声。
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区分不在职业,而在心灵。
某哲人说:朋友如同衣服,会穿旧的,需要时时更新。我的看法正相反:朋友恰好是那少数几件舍不得换掉的旧衣服。新衣服当然不妨穿一穿,但是,能不能成为朋友,不到穿旧之时是不知道的。总在频繁更换朋友的人,其实没有真朋友。
好的友谊必定包含三个因素。
第一是默契。这是灵魂深处的默契,就仿佛两个灵魂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因而双方在基本的价值观上高度一致,彼此心知肚明,尽在不言中。这是一个前提,使得其他方面的沟通也变得容易。
第二是欣赏。这是两个独特个性之间的互相欣赏,所欣赏的是对方身上自己最看重的优点,这优点也许是自己也具备的,因此惺惺相惜,也许是自己不具备的,因此衷心倾慕。
第三是宽容。事实上,只要前两个因素足够强烈,就自然会宽容对方身上自己不太看重的缺点了。如果不肯宽容,就说明前两个因素仍较薄弱。
朋友的朋友一定也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一定也是我的敌人,——这个逻辑未免太简单了一点。
首先它是荒谬的。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朋友的朋友也还有朋友和敌人,以至于无穷,这样我就会有数不清的朋友和数不清的敌人,二者之间还必定有很多交叉和重合。要我接受如此极其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还不够愚蠢。
其次它是幼稚的。友谊的基础是求同存异,每个人都有多面,不同人之间的同异关系不可能划一。我所求之同在你的朋友身上不存在,他就不是我的朋友。我能容你的敌人身上你所不容之异,他就不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只用自己的眼光来辨别敌友,决不用别人的眼光,哪怕这个别人是我的好朋友,这样最简便,往往也最可靠。
人以群分,朋友圈的形成似在情理之中。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圈应该是松散而不定形的,你不要把它弄成一个组织。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友谊最自由,最讲究志趣相投,距离组织最远,把它弄成组织就太不好玩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有许多朋友,但我不属于任何朋友圈。当然会有这种情形,我的若干朋友彼此也是朋友,但我和其中每人的关系仍是非常个人化的,不会受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
友谊是宽容的。正因为如此,朋友一旦反目,就往往不可挽回,说明他们的分歧必定十分严重,已经到了不能宽容的地步。
只有在好朋友之间才可能发生绝交这种事,过去交往愈深,现在裂痕就愈难以修复,而维持一种泛泛之交又显得太不自然。至于本来只是泛泛之交的人,交与不交本属两可,也就谈不上绝交了。
在任何两人的交往中,必有一个适合于彼此契合程度的理想距离,越过这个距离,就会引起相斥和反感。这一点既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谊。
也许,两个人之间的外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们之间情感上的吸引力达到最佳效果。形式应当稍稍落后于内容。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健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靠的是尊重,而不是爱。道理很简单:你只能爱少数的人,但你必须尊重所有的人。
爱你的仇人——太矫情了吧。尊重你的仇人——这是可以做到的。孔子很懂这个道理,他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
爱情和友情是人生的美酒,如果时间短暂,也有新酒的甘甜和芳香。可是,倘若能经受住漫长岁月的考验,味道就会越来越醇厚,最后变成了无比珍贵的陈年佳酿——亲情。恋人或朋友好到了极致,就真正是亲人,比血缘更亲。
读书如交友,但至少有一个例外,便是读那种传授交友术的书。
交友术兴,真朋友亡。
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外倾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很多朋友,但真朋友总是很少的。内倾者孤独,一旦获得朋友,往往是真的。
和太强的人在一起,我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太弱的人在一起,我会只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和强弱相当的人在一起,我才同时感觉到两个人的存在,在两点之间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你与你的亲人、友人、熟人、同时代人一起穿过岁月,你看见他们在你的周围成长和衰老。可是,你自己依然是在孤独中成长和衰老的,你的每一个生命年代仅仅属于你,你必须独自承担岁月在你的心灵上和身体上的刻痕。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但解除孤独毕竟只能靠相爱相知的人,其余的人扰乱了孤独,反而使人更感孤独,犹如一种官能,因为受到刺激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孤独和喧嚣都难以忍受。如果一定要忍受,我宁可选择孤独。
学会孤独,学会与自己交谈,听自己说话,——就这样去学会深刻。
当然前提是:如果孤独是可以学会的话。
心灵的孤独与性格的孤僻是两回事。
孤僻属于弱者,孤独属于强者。两者都不合群,但前者是因为惧怕受到伤害,后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超群卓绝。
孤独是因为内容独特而不能交流,孤僻却并无独特的内容,只是因为性格的疾病而使交流发生障碍。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又不陷于孤独,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尽管注定孤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的可怕和难以忍受。上帝给了他一颗与众不同的灵魂,却又赋予他与普通人一样的对于人间温暖的需要,这正是悲剧性之所在。
越是丰盈的灵魂,往往越能敏锐地意识到残缺,有越强烈的孤独感。在内在丰盈的衬照下,方见出人生的缺憾。反之,不谙孤独也许正意味着内在的贫乏。
孤独与创造,孰为因果?也许是互为因果。一个疏于交往的人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个人专注于创造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
那些不幸的天才,例如尼采和凡高,他们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无人理解,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是可以用创造来安慰的,而恰恰在于得不到普通的人间温暖,活着时就成了被人群遗弃的孤魂。
孤独者必不合时宜。然而,一切都可以成为时髦,包括孤独。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例如牢狱和疾病之灾,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今日的许多教徒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
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完全孤独。天才的孤独是指他的思想不被人理解,在实际生活中,他却也是愿意有个好伴侣的,如果没有,那是运气不好,并非他的主动选择。人不论伟大平凡,真实的幸福都是很平凡很实在的。才赋和事业只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优秀,不能决定他是否幸福。我们说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天才,泰戈尔是一个幸福的天才,其根据就是在世俗领域的不同遭遇。
无聊、寂寞、孤独是三种不同的心境。
无聊是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消遣。寂寞是自我与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是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理解。
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
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
无聊是喜剧性的,孤独是悲剧性的,寂寞是中性的。
无聊属于生物性的人,寂寞属于社会性的人,孤独属于形而上的人。
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无值得别人理解的内涵,因而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孤独。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是悲剧性的。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它是喜剧性的。寂寞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可得,它是中性的。然而,人们往往将它们混淆,甚至以无聊冒充孤独……
“我孤独了。”啊,你配吗?
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未曾体味过孤独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
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
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那些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
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爱和孤独其实是同一种情感,它们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愈是在我们感觉孤独之时,我们便愈是怀有强烈的爱之渴望。也许可以说,一个人对孤独的体验与他对爱的体验是成正比的,他的孤独的深度大致决定了他的爱的容量。孤独和爱是互为根源的,孤独无非是爱寻求接受而不可得,而爱也无非是对他人之孤独的发现和抚慰。
在爱与孤独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现实的人间之爱不可能根除心灵对于孤独的体验,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也不应该对爱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一旦没有了对孤独的体验,爱便失去了品格和动力。在两个不懂得品味孤独之美的人之间,爱必流于琐屑和平庸。
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回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凡是领悟人生这样一种根本性孤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爱得最热烈时也不会做爱的奴隶。
一切爱都基于生命的欲望,而欲望不免造成痛苦。所以,许多哲学家主张节欲或禁欲,视宁静、无纷扰的心境为幸福。但另一些哲学家却认为拼命感受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才是幸福,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爱和孤独都是享受。
人在世上是需要有一个伴的。有人在生活上疼你,终归比没有好。至于精神上的幸福,这只能靠你自己,——永远如此。只要你心中的那个美好的天地完好无损,那块新大陆常新,就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幸福。
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
独身的最大弊病是孤独,乃至在孤独中死去。可是,孤独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享受,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能完全免除孤独的痛苦,却多少会损害孤独的享受。至于死,任何亲人的在场都不能阻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死在本质上总是孤独的。
当我们知道了爱的难度,或者知道了爱的限度,我们就谈论友谊。当我们知道了友谊的难度,或者知道了友谊的限度,我们就谈论孤独。当然,谈论孤独仍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有人独倚晚妆楼”——何等有力的引诱!她以醒目的方式提示了爱的缺席。女人一孤独,就招人怜爱了。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是男人的本分。
我把我的孤独丢失在路上了。许多热心人围着我,要帮我寻找。我等着他们走开。如果他们不走开,我怎么能找回我的孤独呢?如果找不回我的孤独,我又怎么来见你呢?
当一个孤独寻找另一个孤独时,便有了爱的欲望。可是,两个孤独到了一起就能够摆脱孤独了吗?
孤独之不可消除,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求。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奔走的人,最终就会看破小爱的限度,而寻求大爱,或者——超越一切爱,而达于无爱。
爱可以抚慰孤独,却不能也不该消除孤独。如果爱妄图消除孤独,就会失去分寸,走向反面。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
有两种孤独。
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
前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上帝和神圣的爱,或者遁入空门。后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他人和人间的爱,或者陷入自恋。
一切人间的爱都不能解除形而上的孤独。然而,谁若怀着形而上的孤独,人间的爱在他眼里就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深度。当他爱一个人时,他心中会充满佛一样的大悲悯。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他又会发现神的影子。
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了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种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它是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相遇,既充满爱,又尊重孤独;相反,后一种交往则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场”,既亵渎了爱,又羞辱了孤独。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
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
从茫茫宇宙的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偶然地来到世上,又必然地离去。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孤独境遇,才有了爱的价值,爱的理由。人人都是孤儿,所以人人都渴望有人爱,都想要有人疼。我们并非只在年幼时需要来自父母的疼爱,即使在年长时从爱侣那里,年老时从晚辈那里,孤儿寻找父母的隐秘渴望都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仍然期待着父母式的疼爱。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到与我们一起暂时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亲人,都是宇宙中的孤儿,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大悲悯,由此而生出一种博大的爱心。我相信,爱心最深厚的基础是在这种大悲悯之中,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譬如说性爱,当然是离不开性欲的冲动或旨趣的相投的,但是,假如你没有那种把你的爱侣当作一个孤儿来疼爱的心情,我敢断定你的爱情还是比较自私的。即使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其中最刻骨铭心的因素也不是受了养育之后的感恩,而是无法阻挡父母老去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父母作为无人能够保护的孤儿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你的眼前。